男女主角分别是刘清宁王静的其他类型小说《两万里路云和月完结文》,由网络作家“茹若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正感慨,屋外响起王美莲大声的嚷嚷:“什么?哎哟,他们这一家子,这还让不让人消停了!”两人对视一眼,跳起来跑出去问:“怎么了怎么了?”王美莲挂了电话,拎起包对吴正洋说:“双双说丽琴跟她大哥一家到医院去看妈,不知怎么地吵起来动了手。”双双是吴楚楚的表姐,在人民医院当护士,“老二把丽琴的头给打破了,丽琴闹起来,说要离婚!”众人齐声“啊”了一声。王永梅老嬢嬢服毒进了医院的消息,没半天功夫就传到了隔壁村李丽琴娘家。这下李丽琴慌了。在农村,逼死婆婆这样的罪名比天还大,是要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,抬不起头的。后来消息又传来,说老嬢嬢抢救及时,没死成。李丽琴松了口气,在家想了半天,盘算着晚上医院人少,拉着哥嫂一起来看老嬢嬢,想看机会找个台阶,把这事悄无...
《两万里路云和月完结文》精彩片段
正感慨,屋外响起王美莲大声的嚷嚷:“什么?哎哟,他们这一家子,这还让不让人消停了!”
两人对视一眼,跳起来跑出去问:“怎么了怎么了?”
王美莲挂了电话,拎起包对吴正洋说:“双双说丽琴跟她大哥一家到医院去看妈,不知怎么地吵起来动了手。”双双是吴楚楚的表姐,在人民医院当护士,“老二把丽琴的头给打破了,丽琴闹起来,说要离婚!”
众人齐声“啊”了一声。
王永梅老嬢嬢服毒进了医院的消息,没半天功夫就传到了隔壁村李丽琴娘家。
这下李丽琴慌了。
在农村,逼死婆婆这样的罪名比天还大,是要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,抬不起头的。后来消息又传来,说老嬢嬢抢救及时,没死成。
李丽琴松了口气,在家想了半天,盘算着晚上医院人少,拉着哥嫂一起来看老嬢嬢,想看机会找个台阶,把这事悄无声息的抹了,没想到又吵了起来。
“他们怎么在医院打起来了,等下要被医院赶出去。”王静手足无措。
“可不是。丽琴那两兄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,唉,你说这都是什么事!”王美莲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突地疼,“正洋,去开车,我们得去医院一趟,去晚了,医院真要把老嬢嬢赶出来。”
刘清宁连忙说:“我也去。”
“小孩子在家里呆着,我跟你妈去就行。”王美莲拔高音调,不耐烦地:“正洋,走啊!一生世这么摸摸拖拖!”
“那这饭......”吴正洋扔了锅铲,解了围裙,一边嘟囔“你们这一家子!可惜了我买的好黄鱼!”
“砰”地门关上了,留下两姐妹面面相觑。
吴楚楚摇摇头:“我的老天爷,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老王家要家变喽!”
刘清宁哭笑不得:“你怎么有点幸灾乐祸。”
“我可没有。”
“我们也走吧!”
“去哪儿?”
“去医院呀!”
“哎,大人的事你少管——行吧,看在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的份上!”
两姐妹赶到医院,车子还没进停车场,就看见医院大门口围着一堆人,广场上的音响里播着广场舞的舞曲,人却全没了,都围在那头看热闹。
“不会吧,这脸可丢大了。”吴楚楚咕哝。
停好车赶过去一看,果然是自家人。一个农村打扮的精壮老头正抡着拳头要揍二舅,那正是二舅妈李丽琴的大哥李树根。吴正洋扭动着肥胖的身躯吃力地劝着,王美莲和王静不见人影,二舅妈李丽琴呢?坐在地上,正哭天嚎地。
刘清宁多年不见二舅妈了。
她的记忆里,李丽琴是云上村出了名的美人儿,身材纤细,头发烫着时髦的小卷,同样的的确良花裙子,穿在王美莲身上和她身上,是两样的风情。
此时的她,一屁股坐在地上,全然不顾脏乱,双腿不停地蹬着,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地面,一头半花白的短发凌乱,后脑勺上还支棱着几撮,脸上的表情极为丰富,却是一滴眼泪都没有,只是干嚎。
“皇天,皇天哦......”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脏话,两姐妹听得直皱眉头。
刘清宁不禁想,那么漂亮的二舅妈,怎么就变成这幅农村泼妇的模样了?
“我们别过去,丢脸。去看看外婆吧。”吴楚楚扯了扯发愣的刘清宁。
夜晚的医院格外安静,王永梅的病房在走廊的尽头,两姐妹路过护士站,正撞见表姐双双。
“你们俩来了?哎,我真服了你妈那家人了!”双双直抱怨,“害我被护士长一通训。”
“闹得很厉害?”
“热水瓶都砸了!你那个二舅妈哭天抢地的。还有她那个大哥,一把年纪,两个保安都按不住!比你二舅妈还泼!真是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。你二舅被摁在地上揍!要不是保安赶来快,直接进楼下急诊了!还有你外婆,躺在床上直拍床板,输液管都倒流了,一手背的血!”双双边说边摇头。
刘清宁忍不住问:“他们这到底在闹什么?”在医院里闹,实在不像话!
双双仔细看了两眼才把刘清宁认出来:“哎,你回国了?还不就为你外婆养老那点事。你二舅妈说要把你外婆送养老院,你二舅不肯,一言不合,就打起来了!”
还是为这点事。
“送养老院,倒也是一个选择。”刘清宁说。
双双嗤笑一声:“你当养老院是什么好地方?广告看多了吧!那地方进去了,就是等死了!”
“啊?”
“我们这的养老院,有一个算一个,都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不过能怎么办呢?久病床前无孝子,我在医院见多了。有退休金的还能活得有尊严些,像你们外婆这种,只能看儿女良心了!”
一番话说得刘清宁五雷轰顶般。
怎么就等死了,外婆今年才刚刚八十,怎么就等死了?
病房里,王美莲两姐妹正在说话,王美莲说话声又低又急,听不清楚说什么,只听见夹杂着些气急败坏的脏话,王静则只是叹气。
王永梅躺在病床上,没有睡,眼睛木然地瞪着天花板。
见两姐妹进来,王美莲停止咒骂:“你们两个怎么来了?”
“我们来看看。”
“有什么好看的。行,你们俩在这陪陪外婆。”王美莲起身,拉着王静往外走去。
医院的夜很静,两人的声音虽轻,但还是传进病房里。
“要我看,去找找养老院?牛不喝水强按头,今天见丽琴这个样子,把妈留在她家我也不放心,万一以后再......钱我也可以出一点,我跟万信商量商量......”
“这不是钱的问题!你以为送进养老院就不用管了?做人不是这么做的,哦,当年好处都拿了,现在她说不干就不干了?”
“那怎么办呢?等妈出院了,总得有个地方去。”
门外沉默了。
两姐妹坐在外婆的病床旁,相顾无言。老嬢嬢陷在医院发黄的白色被褥里,神情呆滞,也不知她有没有听见。
“外婆,这是宁宁。”吴楚楚大声地说。
老嬢嬢的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,木然机械地落下来,落在刘清宁的身上,半晌没有聚焦。
“宁宁来看你了!”吴楚楚冲着她的耳朵喊。
死鱼般的眼珠子终于翻动了一下,老嬢嬢缓缓地冲刘清宁抬起手来。
刘清宁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住了那只枯柴般的手。那手一点肉感都没有,就像木偶芯子套了层老化发硬的塑料袋。
“你回来了?你妈没回来?”
吴楚楚“啧”了一声:“这老嬢嬢还糊涂着呢。”
“都回来了。”
“人呢?怎么没来?”
“等下就来。”
老嬢嬢的目光露出欣慰的颜色,塑料皮般的手轻轻在她手背上摩挲:“囡囡,在外面饭要吃饱,衣服要多穿!”
一如小时候,每一次挥别老家回城里上学的时候那般的叮嘱。
刘清宁吸了吸发酸的鼻子。
门外王美莲的手机响了两声,她接起来,没两句就叫嚷起来:“谁要她什么老房子,放屁!”
双双匆匆赶过来:“舅妈,你小声点,病区严禁喧哗!”
王美莲还在嚷:“哦,不值钱了她晓得不要了?那年是谁怕我们跟她分拆迁费,追着我们立字据......你告诉她,别那么便宜的事!”
“这位病人家属,请你出去!”
“我妈就是死也要死在她屋里头!”
“妈,你小声点!”
“姨妈,要不然......我留下来照顾外婆吧。”刘清宁说。
阿青婆生于民国初年,长于战争年代。具体的时间没有人记得,应该是1930年以后,她嫁到云上村,没几年,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
那个年代,农村的日子并不好过,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几年,阿青婆的丈夫,陈显华的爷爷陈定为了谋生,丢下家中的妻儿,跟着同村人一起去了欧洲,从此音讯全无。
那个年代青田人出国打工,并不走正道,死在半路上的人不在少数。
阿青婆等了又等,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,村里人都默认他已经死了,还有人劝她趁年轻改嫁,但阿青婆始终没有答应,独自一人将三个孩子养大。
那是个战争的年代,除了应对自然灾害,还要提防时不时从天而降的日军的飞机炮弹。
1942年,日军攻陷青田,云上村虽然偏僻,但没能逃过日军的搜掠。
“我父亲上了年纪之后,身体不好,常年卧病在床,常常同我讲起以前的事。”
那时陈建明已有八九岁年纪,他清楚地记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村搜掠,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躲进屋后的地窖里,年幼的妹妹忍受不了地窖的湿闷,大哭起来,引起了鬼子的察觉,
母亲拼命捂住了妹妹的嘴巴不让她出声才逃过一劫,等鬼子走了之后才发现,因为捂得太紧,妹妹已经闷死在母亲的怀里。
当时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,直到多年以后提起来还心有余悸,而母亲因为闷死了妹妹而愧疚,精神大受打击而病倒。
但即便病倒了,她还是得拖着病体下地干活,挣钱来奉养公婆,照顾两个儿子。
可以想见,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,阿青婆过的是怎样艰辛的苦日子。
后来,红军打跑了鬼子,解放军渡过了长江,成立了新中国,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,大约是五十年代,阿青婆收到了来自西班牙的消息,原来陈定并没有死。
“这事村里人都知道!”李阿四说,“那年我还是个小后生,听我娘说,村里回来个华侨人,是阿青婆的男人,有钱呢!啊哟,不得了,穿西装,打领带,皮箱里都是洋货,后头那座石桥,就是他捐的钱修的,桥头碑上还有字嘞!嘿!原来那就是你阿公!”
那时云上村的人才知道,当年虽然陈定的目的地是欧洲,可是他上错了船,糊里糊涂地跟同村人分开,孤身一人被带到了南美,最后在巴西上了岸。
在巴西,他做过一段时间提包挈卖的营生。
所谓提包挈卖,是海外青田人积累资本最原始朴素的方式。
扛着一个编织袋,装着鞋子、衣服等杂物百货,一家一户地敲门兜售。那时候闯天下的青田人,没有人脉,没有门路,只能从最苦最累的活开始干起。
在提包挈卖的那段日子,陈定认识了一个当地华人的女儿,很快和对方坠入爱河,缔结婚姻。
在新岳父的资助下,两夫妻到了西班牙,开了餐馆,做大生意,赚了不少钱,成了大老板,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
听说了这个消息的阿青婆是什么反应,已无人知,但不难想象。
陈定在云上村住了半个月便走了,这一走就再没回来过。
后来陈定写信来,问阿青婆是否愿意出国,阿青婆拒绝了。
她收下了陈定寄回来的钱,推倒了陈家原本的破牛棚,重新盖了房子,便是现在的陈家老屋。
建新房子的时候,阿青婆只给自己在一楼留了房间,东西两侧各起了二层小楼,留给两个儿子一人一栋。新房建成,又大儿子陈建明娶了老婆,生了一儿一女,阿青婆的脸上,日日都是喜气。
她还有儿子、孙子,村里给她分了地,有田种,有饭吃,日子蒸蒸日上,没了男人,不算什么。
好景不长。
五十年代末,全国上下遭遇了大饥荒,到了六十年代初,生活变得更加艰难。
为了谋出路,陈建明带着妻子和弟弟,搭路子出国投奔父亲,也在西班牙定居,只留下五岁的大儿子和三岁的女儿,也就是陈显华的大哥大姐给阿青婆抚养。
阿青婆不得不又一个人承担起抚养孙子的职责。
70年代末,两个成年的孙子孙女也踏上了去西班牙的路。从此,老房子只剩下阿青太一个人居住。
“一直到新房子变成老房子,然后在这房子里孤零零地去世?阿青婆真是可怜。”刘清宁说道。
“其实,我父亲也想接她到西班牙一起生活。而且他确实也这么做了,在我十多岁的时候,奶奶来过马德里,还住了一年,所以,我对她有一点印象。”
在陈显华的印象中,奶奶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老人。
她一直穿着很旧的蓝布衣衫,是那种传统的中国样式,衣领袖口还绣着中国样式的花纹。
她不会说普通话,更不会说西班牙语,而是讲口音很重的青田方言。
那时候,陈显华不会青田话,如听天书一般,根本无法与奶奶交流。
阿青婆被接到马德里的时候已经年迈。
那时候,陈显华的祖父已经去世,他的继奶奶是陈家的大家长,在马德里,她唯一认识的只有自己许多年未见、并不熟悉、忙于生意的两个儿子和由自己抚养长大的两个孙子孙女。
听到这里,刘清宁忍不住想起了刚到马德里的自己。
当初登上前往西班牙的飞机,阿青婆肯定和她前往马德里之前一样,是对未来的生活抱着一种期待的,她盼望的是与从未谋面的父亲、分离多年的母亲的重聚,期待的是父母疼爱的怀抱,阿青太盼望的、期待的则是母子团聚,一家团圆,从此颐养天年。
但很显然,她们都没能如愿以偿。
父母疼爱的怀抱,是属于她的弟弟妹妹的。而一家团聚颐养天年,则是属于那个抢走阿青婆的丈夫的女子的。
长久的分离,文化的隔阂,是她们和家人之间迈不过去的鸿沟。她们都成了这个家庭的“旁观者”,就像西方电影里那种死去之后留在家里的亡魂。
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愉快。
云林镇里有个云上村。
云上村坐落在海拔600余米的山顶之上,因海拔高,一年四季云雾缭绕,由此得名。
王家老屋在云上村,是姐妹俩的童年乐园。
时间尚早。
吴楚楚的车子驶出城区,驶入省道,沿着瓯江一路朝云林镇的方向开去。
一侧是山,一侧是江。
江面开阔,波光粼粼,清风拂面。
刘清宁坐在副驾驶上,靠着窗,若有所思:“外婆在老屋住了一辈子,是不是?”
“嗯。”
外公是上门女婿,云上村的老屋是王永梅家的祖屋。那年头交通不便,尤其是女人家,很少有机会出门,老嬢嬢这一辈子都没怎么踏出过云上村。
后来外公去世,众子女不放心老嬢嬢独居,由王美莲主持家庭会议,把老大老三名下的老屋和村里的田地都给了老二,两兄弟再各掏五万块,讲明由老二负责给老嬢嬢养老,王永梅千百个不愿,被迫从老屋搬到山下云林镇住。
云林镇早些年是贫困镇,后来政府搞大搬快聚,将山上的几个村子里的村民都搬到了山下的镇里,新农村盖起了新楼房。
一片片规划整齐的独栋小楼,白墙红瓦,十分漂亮。
老嬢嬢住进了新楼房,心里还惦记着老房子。刚开始的时候,每次王美莲去看她,她总要念叨。
“住不惯,我在这里住不惯。美莲,我还是要回老屋去住。”
“你回去住,谁给你做饭吃?在这里住着有丽琴伺候,什么都不用做,天天搓麻将,太舒服了?”
“我自己做饭吃。”老嬢嬢倔着。
王美莲生气了,拉下脸骂她:“你这老嬢嬢,别说胡话!”
王永梅最怕这个女儿,挨了骂就不敢吱声了。等王美莲走了,她自己收起衣服,揣着个小包跑回老屋去。到了晚上不见人,李丽琴去找才发现老嬢嬢不见了,慌得报了警,找到半夜,在半山腰发现一脚踩空摔下去的老嬢嬢。
王美莲气得半死,把老嬢嬢好一通骂,骂得老嬢嬢害怕了,再不敢提回老屋去住的事。
这一下就过去了好几年。
这些事,刘清宁都听吴楚楚提过。
那天王静回家换洗,刘清宁接班陪着外婆,祖孙俩聊天,王永梅抓着刘清宁的手直叹气:“我是没几年活了。我跟你大姨说,等我以后死了,要把我和你外公的牌位放老屋里去。”
“外婆,你还年轻呢。现在的人都长寿,活到九十一百都有的。”
“活不到喽!还是你外公命好,死在老屋里,我是没指望了。”老嬢嬢直叹气。
刘清宁就想,既然二舅妈又不愿意外婆留在自己家,外婆也想回老屋去住,那搬回去岂不是皆大欢喜?
谁料到这个想法没有得到除了老嬢嬢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的赞同。
吴楚楚一打方向盘,从省道驶进路边一条不起眼的小路,开了一会儿,刘清宁才分辨出,这就是当年回云上村的老路。
“你妈都在我妈面前哭了四五回了,把我妈愁的。”吴楚楚说。
刘清宁提出要留下来照顾外婆,不回马德里,王静已是强烈反对。没过两天又说要接手村里的老屋,带外婆回老屋去住,王静血压一高,险些晕过去。
王家的老屋在云上村,从青田县城过去,省道走完走县道,县道走完爬乡道......那可真是个山沟沟。
早些年外公还没去世,老两口还住在云上村,逢年过节还走动走动,后来老嬢嬢下山住,王家人就再没回老屋看过。
听说村子早就荒了。
王静与女儿不亲,不敢开口,在王美莲面前抹了好几回泪,王美莲不忍心,勒令吴楚楚劝刘清宁回心转意。
吴楚楚奉命与刘清宁长谈几夜未果,倒把自己折腾得严重睡眠不足。
凭心而论,吴楚楚想刘清宁留下来。这个妹妹是真正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,亲妹妹一样。亲妹妹在外面过得不开心,当然希望她回家来。
将心比心,她也能理解,哪个父母能同意自己大学毕业的孩子丢下国外的工作和父母,到山沟沟去过日子。
山路十八弯。
六十年代之前,从云林镇到县城只有山路,乡民进城全靠两只脚。六十年代末,政府在云上村村口修了一条乡道,连接县城到云林镇。
云林镇成了云林镇进城的必经之路。
俗话说,要想富,先修路。因着这条乡道,云上村繁华热闹起来,一度成为云林镇最繁华的村子之一。
八九十年代,青田掀起了一股新出国热,村里的青年人大多都出了国,政府又开始搞大搬快聚,动员山上偏僻村子的村民下山脱贫,剩下的村民也陆续搬到了镇上,村子逐渐衰落。前几年,国道线从云林镇修过,一条2000余米的隧道从山脚通过去,直接连接了县城和小镇,而不需要再经过云上村,从县城到云林镇更加方便,村子彻底荒芜。
到如今,云上村已经是个“空心村”。
在刘清宁的印象里,从县城到云上村距离县城是一段非常遥远的车程。
那时候吴正洋还没买车,每次王美莲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,需要去汽车站坐小巴。
半个小时一班车,混杂着柴油和家禽味儿、汗臭味的车子在盘山的公路上低吼着爬一个小时,爬上了山顶,再巍巍颤颤地溜半个小时的坡,直到刘清宁的胃在胸腔里翻江倒海,未消化的食物顶到了喉咙,往往是车子还未停稳,她便冲下车蹲在路边狂吐。
虽然外婆家是她童年美好的回忆,但去外婆家的山路却是她童年的阴影,回忆有多美好,阴影就有多大。
幸而现在修了路,车子拐下国道,沿着盘山小路上爬了十几个之字大弯,终于停在了云上村村口的千年古樟树底下。
二十来岁的模样,穿着T恤衫牛仔裤,清瘦,身姿挺拔,站在一堵矮泥墙上,双手插在腰上,一笑,露出一口白牙来,便显得他皮肤有点黑了。
有点眼熟,却记不起来。
“陈镇长,你取笑我呢!”吴楚楚向刘清宁介绍,“这是我高中同学陈今越,现在在云林镇挂职副镇长。那天外婆喝了药,就是他开车送到县医院来的。”
刘清宁想起来了,在医院见过,她还喝了他一杯咖啡。
“你好。谢谢你!”她连忙道谢。
陈今越从矮泥墙上跳下来:“谢什么,职责所在。”
几只狗与他显然是旧相识,立刻解除了警戒,摇头晃尾地围了上去。
陈今越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包狗饼干,边走边喂:“今天怎么到村里来了?”
“这是我表妹宁宁,出国十几年了第一次回国,所以我带她回老屋看看。你今天怎么在这里?”吴楚楚问。
“县里想要开发云上村的事,你该知道吧?”
吴楚楚点头:“知道。”
“今天来了个上海的考察团队,县长亲自陪同,刚走。”
“有戏吗?”
“没戏。”陈今越干脆利落。
吴楚楚笑:“没办法,这里交通不便,基础设施也落后,在这里投资,成本高、收益低的项目,自然不是他们的选择。”
“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干呐。”陈今越感叹,“撸起袖子加油干,踮起脚尖摘桃子......如果今年还招不到商,年底考核又是垫底。我们镇里已经连续好几年垫底了,这面子里子都不好看。”
他有些烦躁地挠挠头。
尽人事,听天命吧。
刘清宁静静地听着,没说话。
云上村的这些老房子,对于她来说是童年的回忆,但对于与它无关的人来说,只是一堆破木头和烂污泥。
她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“或许再过十年,二十年,地球上就不会再有这个叫作云上村的村子了吧。”
到那时候,那些和她一样少小离家,远渡重洋的人,他们与家乡的维系会不会也随着老屋的消失而消逝呢?
陈今越点头。
“如果一直找不到投资商,等到这个村子最后留守的几位老人都走了,这个村子或许就真的彻彻底底结束了它的生命了。”
吴楚楚惊讶:“这村里还有人住?”
那刚才看到的那个不是鬼?
“当然。”陈今越看了看手表,十点半,“走吧。”
“去哪儿?”
“你难得回来一趟,带你们去路寮坐坐,认认人。”
路寮是建在路上的亭子。
从前山里交通落后,六十年代末乡道通车之前,村民外出探亲访友、买卖货物都靠两只脚翻越山岭,动辄便是半日的路程,因此在一些路口要道,岭头、岭脚,百姓捐钱出力建起路寮,供过路行人歇脚喝茶之用。
八九十年代,云上村还有三座规模较大的路寮,现在没人走山路,路寮失去了作用,风吹雨打,倒的倒,拆的拆,只剩下村子里的一座。
“我记得那座路寮,就在桥头。”刘清宁回忆着。
清源溪从王家老屋的后山上起源,途径云上村,将整个村子一分为二。溪上搭着一座简朴的廊桥,桥头附近便是一座路寮。
就着路寮的便利,老屋的主人在一楼的门店开起杂货店。那时的杂货店不像现在的超市开架售卖,门后便是一个玻璃柜台,柜台上还摆放着一个个圆玻璃罐子。
柜台里和老板身后的货架上的杂货,小孩子们并不关心,但圆玻璃罐子里的饼干、瓜子、糖果,油枣、巧食、炒米,总令他们垂涎三尺。
小时候两人经常捏着外公给的几分钱,小兔子一样欢快地蹦跳到店里,迫不及待地将几分钱交到老板的手里,换几块饼干,或一小杯瓜子。
“这村里还真有人住?”吴楚楚边走边问。
“当然有。”陈今越的步子大,却闲闲地落在她俩身边,三人并排,将小路挤得满满当当。那几只大黄狗,早跑到了前头。
两姐妹互看一眼,无声地抿抿唇笑。
看来刚才看到的不是鬼。
桥头路寮就在河对岸。
村里没了人烟,桥头商店早就倒闭,前些年被村里征用,修了个村民活动中心。李阿四身受重托,成了活动中心的“管家”,日复一日,天没大亮就起来,点蜂窝煤,烧开水,煮大碗茶。等他将路寮里外都扫干净,村里人便陆续来了。
或坐着闲谈,或搓麻将,打棋对。
后来村里人越来越少,到最后一桌麻将也凑不起来,李阿四的大碗茶也越煮越小锅。
这天他刚给茶壶里续上水,一抬头,就看见陈今越在河对岸,带着两个年轻小姑娘朝这边走过来,大声打招呼:“陈镇长,过来喝茶哦!”
陈今越远远听见,朝他挥手。
李阿四背着手,挺起驼了半辈子的背,眯着眼睛远眺,自言自语:“嘿,今天带了两个漂亮后生囡。”
刘清宁跟着进了路寮。
说也奇怪,刚才一路走来阳光灼人,一踏进路寮,不知从哪里吹来阵阵清风,一路的疲累炎热一扫而光。
李阿四早从屋里端出三个粗陶碗来,倒了三碗茶水。
茶是凉茶,用村里自己晒干的草药泡的,小时候只觉得这茶味道苦,长大了再喝,却品出丝丝甘甜来。
刘清宁一口气喝了个见底,抬眼一看,一楼店门上黑漆刷的几个字还在:桥头商店。
除此之外,店里全变了样子。四方的屋子,两面开门,两面靠墙的两排柜子还在,全落了灰。门头的玻璃柜子也在,空的。柜台上的圆玻璃罐已经搬走了,柜台上放了一部暗红色的固定电话,电话上也落了灰。
屋里摆着三四张麻将桌,没有麻将,散落着几件杂物和几副扑克牌,一台大彩电,盖着白色蕾丝桌布。
李阿四是个精瘦的老头子,个子不高,又有些驼背,显得更矮了,身上套着一件又旧又破的背心,嘴巴张个不停,不是大声说话就是小声嘟囔,活脱脱就像《哈里波特》电影里的老精灵克利切。
吴楚楚认得他,从前就住在王家老屋附近,虽然两家没有亲戚关系,但同一个村子论辈分叫,他得管王永梅叫姨。
李阿四刚过七十,腿有些残疾,打了一辈子光棍,无儿无女。
年轻的时候,李阿四在镇里的小学当过老师,教语文,也教过王美莲和王静姐妹,后来因为没有教师资格证,被学校清退失了业。
他腿脚有残疾,干不了重活,失业之后成了低保户。前些年村里给他找了活,让他负责云上村的保洁,每周两趟,骑一辆小三轮把村里的垃圾送到下林村的垃圾收集点。村民活动中心修好以后,他又负责每天开门关门,烧水打扫,一个月一千多的收入,够自己吃喝。
这些都是听王美莲说的。
云林镇政府大院坐落在长街的尽头,拐个弯,便是成片的农田。
钟文焕一大早亲自在田里巡了一圈,劝了一圈。劝什么?禁止焚烧秸秆枯枝。成效不大,骂挨了不少。
那些村民当然不敢骂,点头哈腰说“好好好,一定配合工作”,等他一扭头,祖宗十八代都给你骂完了。
他假装没听见,憋了满肚子气,回到办公室,找茬发了一通火,陈今越来报告工作的时候,脸色还跟锅底一样。
“怎么又把这个翻出来了?”
钟文焕翻着陈今越递过来的材料,云上村老屋拯救计划,粗粗一看,发现修改了不少,新增加了不少今年省里、市里的新提法、新政策。
看来这家伙一直没放弃。
“云上村老屋拯救计划”是陈今越到镇里来之后,在各个村跑了两个月,提出来的第一个工作计划。
他认为,要招商投资云上村,必须先把云上村的基础打扎实。现在的云上村,破落村子一个,谁看得上?
但这个计划一直没通过镇里的同意,原因很简单,钟文焕反对。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,没钱。
云林镇是全县经济最困难的乡镇之一。
要修路,要修桥,要翻修老屋......人力物力,哪样不要钱?
要是换了别人,钟文焕直接瞪眼就骂,但这陈今越是市里下放锻炼的干部,过几年那是要回去的,到时候再来,那可就是领导了,得罪不起。
“今越啊,我知道你一门心思想要发展云上村是好意,”钟文焕端着包了浆的玻璃茶杯,慢条斯理,“但这个事牵扯的面太广,资金口子大,我们还得多考虑考虑。眼下你还是想想办法,把那老太婆的事情搞定......”
“我搞定了。”陈今越说。
钟文焕一愣,怀疑自己听错了。“你搞定谁了?”
“纸板婆呀。我跟她都谈好了,明天下午,她来镇里签字画押。”
钟文焕拍了下自己脑门,确定不是早上怒火攻心,神志不清了。纸板婆的事,镇里前前后后拖了有两三年,这才交给这小子半年,办好了?
他不信,别是骗他的。
“一块地基?”
“就一块地基。”陈今越往椅子上一靠,得意劲儿十足。
纸板婆果然如约来签了字。
签字那天,镇里上下都来围观。
纸板婆到得准时,她特意洗了澡,换了身干净衣裳,乱糟糟的头发洗得干干净净,反倒显得更花白了。
进门的时候,镇里人险些没认出来。
钟文焕感叹,自己接访这老嬢嬢一年多,今天才看清楚了老嬢嬢的真实面目。
边上有人笑:“钟领导,别说你没见过,我就在这村里住了这三十多年,我也没见过!”
在众人的哄笑中,老嬢嬢郑重地签完字,起身对着陈今越千恩万谢,要不是人拦着,当场就要跪下去了。吓得陈今越连忙跳开,说阿婆,这不是旧社会了,不流行跪拜这一套。
纸板婆说,领导,你对我有大恩,以后有空上我们家来,我给你炖蒲蹄肉吃!
陈今越连连说好。
纸板婆走了,陈今越将协议书往钟文焕面前一丢,样子得意:“钟领导,说话算话。纸板婆签了字,你就批我的老屋修复计划。”
钟文焕接过协议书,看着上面红彤彤的手指印,心头一块大石总算落了地。拿着这份协议书,总算能向县里交差,其他的什么都不算事了。
钟文焕心里高兴,忍不住笑骂:“你小子!年轻人的脑子是灵活。行,你准备材料,下次会议,议一议。”
纸板婆签了字的事在镇里传开,人人都称奇。
镇里人都说,这下两个大女儿估计要跟纸板婆闹翻了。谁料到从那以后,两个女儿时不时地上门,一口一个“妈”叫得亲热,打扫洗衣做饭,抢着干,比从前还勤快,叫人跌破眼镜。
这小陈镇长,是传了什么大法给纸板婆了?
看来这空降兵还有两把刷子。
那你说,他能把云上村的事搞定吗?
这可难说,那村里还有那癫人呢!
大樟树底下,村民们议论纷纷。兰香面馆外,吴鑫一边听着这些议论,一边慢悠悠地吃着山粉蛋面。
吃完,抹一抹嘴。“我走了!”跟姑姑吴兰香打了个招呼,骑上小电驴,慢悠悠地晃回到镇里。
一进办公室,跟同事小叶撞了个满怀。小叶手里拿着笔记本:“你还慢悠悠地,开会了!”
“开什么会?”
“陈镇召集的,你没看通知?”
吴鑫嘟囔:“镇里开会,什么时候叫我了?”翻出浙政钉一看,果然有他,未读,还被DING了一下。
云上村老屋拯救计划专班小组会。
毛病。他什么时候进了这个什么专班了?吴鑫打开协同办公系统,翻了一会儿,从已办文件里找到自己懒得打开看的成立专班小组的通知,才发现原来自己真是成员。
吴鑫没去开会,扭头进了办主任老林的办公室。
“他陈今越是什么意思?故意耍我?”
老林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:“哎,你这个脾气!别这么直呼领导名字,注意影响。”
“怎么了?他妈取名字不是让人喊的?三十出头的毛小子,我在镇里干的时候,他还不知道在哪呢!”
老林翻个白眼:“年纪大管用吗?我们院里,门卫老陈年纪最大,云林镇归他管了?官大一级压死人。人家高你三级!”
吴鑫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
老林语重心长:“老吴,难道你这辈子就真打算这么混下去了?难得陈镇肯用你,你不想着好好表现,在这里鬼叫什么?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!”
“我知道啊,所以才替你惋惜!”老林摇头。“你别管他是什么用意,总比你现在,跟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的好。就算不为了争口气,你也为了钱呐——差一级,以后退休金差不少呢!”
老林这话,吴鑫没法反驳。
从老林办公室出来,楼上正好散了会,小叶笔记本夹在胳肢窝里,噔噔噔地下楼梯,见了他,又问:“你怎么没来开会?陈镇还问你了。我说你家里有事,回去一趟。你可得谢谢我,替你打了掩护。”
小叶说完就跑了,吴鑫慢吞吞地跟进办公室,假装擦了一会儿桌子,才若无其事地问:“刚才我没去开会,陈镇没提?”
小叶头也没抬:“没提。”
吴鑫闹不清楚这小子到底唱的是哪一出,直到下了班,陈今越也没来找他,他一改往常踩着点溜的习惯,慢吞吞地骑上小电驴,磨蹭了几分钟,才慢悠悠地沿着长街往兰香面馆的方向骑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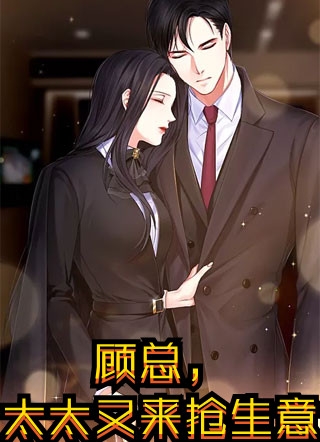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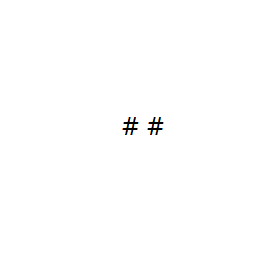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