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陈渺然陈远然的其他类型小说《江岸村的龙凤胎后续+完结》,由网络作家“我有嘉鱼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1976年9月,骄阳似火,烈日炎炎。江岸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,正在地里热火朝天的摘南瓜,公社司机正在公路边等着装货上车,把南瓜拉去市区卖钱,补贴公社的各种集体开销。等完成大队长布置的采摘任务,众人身上的粗布短袖都被汗水侵透了底,但脸上难掩喜悦的笑容。大家伙扛着锄头,背着背篼,成群结队地走在乡间小道上,三三两两的说笑着,一道去集体食堂吃晚饭。不过,大多是知青和知青聚在一堆,江岸村村民和村民走在一起。有女知青突然扯到了晚饭:“我听李队长跟江岸村的人说,今晚食堂吃回锅肉,不晓得是不是真的?”“我们公社前不久刚卖了二十头猪,小猪娃些都没有长大,哪里有肉给我们吃?”身边的男知青哂笑一声,随即话风一转,“不过嘛,要是江岸村有喜事,别说回锅肉了,红...
《江岸村的龙凤胎后续+完结》精彩片段
1976年9月,骄阳似火,烈日炎炎。
江岸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,正在地里热火朝天的摘南瓜,公社司机正在公路边等着装货上车,把南瓜拉去市区卖钱,补贴公社的各种集体开销。
等完成大队长布置的采摘任务,众人身上的粗布短袖都被汗水侵透了底,但脸上难掩喜悦的笑容。
大家伙扛着锄头,背着背篼,成群结队地走在乡间小道上,三三两两的说笑着,一道去集体食堂吃晚饭。不过,大多是知青和知青聚在一堆,江岸村村民和村民走在一起。
有女知青突然扯到了晚饭:“我听李队长跟江岸村的人说,今晚食堂吃回锅肉,不晓得是不是真的?”
“我们公社前不久刚卖了二十头猪,小猪娃些都没有长大,哪里有肉给我们吃?”
身边的男知青哂笑一声,随即话风一转,“不过嘛,要是江岸村有喜事,别说回锅肉了,红烧肉都吃得上,还能吃上九大碗,接连饱餐好几顿。”
河边的古老石桥上,用红油漆写着方方正正的一行字: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”
从城里下乡的几位知青,在扫见那句话后,眼色陡然变得不善,视线越过高低起伏的人群,最终落在前方一道绿色尖尖上。
为了贯彻“吃苦耐劳”的奋斗精神,那怕满头大汗,大家伙都没戴遮阳的头巾。因此,那顶用芭蕉叶制成的草帽显得格格不入,很遭人唾弃。
一位女知青忍不住骂道:“都说劳动最光荣,这地主家的小姐一副享乐怕热的做派,比我们城里人还讲究。”
“她天天拿着课本不放,最近又和北京来的男知青走的很近,说不定,人家是真的想当城里人呢!”男知青添柴加火的回道。
身边人十分震惊:“我听村里人讲过,陈渺然和赵迢从小定了娃娃亲,哪怕赵迢进了部队当兵,都不嫌弃陈家,她竟然背着赵迢勾搭上城里人,这种忘恩负义的女人,就该被教育!”
“我赞同,陈渺然同志必须经受精神和劳动的双重改造,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好战士,和我们一起建设人民公社。”
经过一番慷慨激昂的讨论。
知青们决定趁着明天上午休息,在中学操场门口举办一场教育会,专门教育陈渺然,并让其家人进行深刻反省。
而走在最前方的陈渺然,浑然不知即将到来的风雨。
她右手提着锄头,左手提着一个大南瓜,背篓里装满刚割的猪草,一张白皙的小脸热得通红。
她望着身旁的中年妇女,语气催道:“三姑,你快把我头顶的绿帽子拿下来,不然那些城里人看见了,又要骂我是地主小姐了。”
“咿......水苗热,我不......不取。”
中年妇女像孩童一样傻笑着,一边用芭蕉叶扇风,面部表情很是迟钝和天真,明眼人一看便知,她脑子不太好使。
陈渺然长叹一口气,商量正事:“三姑,你待会儿把饭压紧些,带回家给奶奶和幺爷吃,好不好?”
中年妇女结巴道:“我......我给娘带…饭,吃饭。”
说罢,还高兴的摆了摆她手边的竹篮,在藏蓝色粗布的掩盖下,里面装着三个斗大的陶碗,正是姑侄俩吃饭的活计。
陈渺然领着三姑来到食堂,她放好竹篮和背篓,从竹篮里掏出两个陶碗,和三姑分别排在不同的队伍,今日负责打饭的五六个人,都是江岸村土生土长的村民。
所以,他们对陈渺然和三姑的行为,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不过,在给三姑打饭时,热情的同村婶子是压了又压,直接堆成了小山丘。
知青们看见这一幕,嚷嚷道:“我要向队长举报,你们区别对待知青和本村人。”
“她一个妇道人家,哪吃的了那么多,凭啥子给她打那么多。”
陈渺然把饭碗放好,她直接对着吼的最大声的人,戳心窝子道:“我姑今天摘南瓜得了第一,你们当中任意两个人加起来,都比不上我姑摘的总量,干得多,吃的多,我姑为啥子不能多吃?”
知青们愤愤不平道:“她就是不能多吃,这是贪婪粮食。”
“陈渺然,你们两个人打三个饭碗,太贪心了,必须把生产队的粮食还回来!”
“对,还回来,赶紧还回来。”
在没实行土地改革以前,江岸村的男女老少,或多或少都受过陈家地主的帮助。
更何况,村里人大多数都姓陈,虽然主家落败,但也容不得别人瞎说。
特别是这从成都来的八九个知青,天天借口腰痛腿酸不干活,在村长放电影时,总是莫名其妙的发出笑声,简直败坏心情。
江岸村的人帮腔道:“我们三姑吃的是生产队的粮食,我们都同意她多吃,你们凭什么不让她吃饭?”
“三姑插秧是最快的,摘南瓜是最多的,砍柴是最重的,我们三姑年纪大了,就爱吃饭......”
“人家干的多,吃得多,总比你们干的少吃的多,吃不完还偷偷喂狗的行为,光明磊落。”
食堂里,气氛涌动。
知青们被江岸村社员的那一句“你们城里人就爱斤斤计较”,被噎得说不出来话,气势顿时软了一大截。
就在这时,打饭的婶子夺过知青的饭碗,满满实实的打了一大碗,道:“小伙子,你带着这碗饭回宿舍吃,千万别撑坏了你们养的那条狗,那条胖狗都快赶上我家养了两个月的猪。”
话里话外,满是嘲讽之意。
知青们端着满满当当的米饭,愤怒地回到宿舍,等吃完最上面的那层薄薄的回锅肉,突然“啪”地把筷子拍在桌上,屋里传来窃窃私语。
不知过了多久,门缝打开,从宿舍里面跑出来了两三个人,他们提着油灯,忽略院子响亮的狗叫声,分别往不同方向去了。
看那方向,好像是去另外两支生产队的知青宿舍。
睡在陌生的环境,旁边躺着一个滚烫的活人,陈渺然醒的很早,她害怕被赵母发现两人分开睡的事情,想着先把凉席收起来,但收的太快太急,手指不小心被草绳割除一条口子。
她顿时来了气性,推了一把睡得正熟的青年,喊道:“赵迢,我们该起床挣工分了,你赶紧把凉席藏好。”
“起,我这就起。”
赵迢睁开眼睛,视线雾蒙蒙的,显然还没天亮,稀奇道:“小渺,士别三日,当刮目相待,你今天起这么早种地,委实让我高看你一眼”
“废话,要是去迟了,只能干挑粪背的活。”
办酒席之前,村长把几人的生产队关系进行了调动,陈渺然从一队转到三队,赵芸和陈远然从三队转到一队,还给陈远然安了一个计分员的名头。
最近是收苞谷的月份,等苞谷从地里背出来,晒干后,就要按照工分排名分粮食。
两人来到灶房,陈渺然负责烧火,赵迢负责热菜,赵迢望着满脸通红的新婚妻子,又起了话头。
“小渺,早知道我们两人会结婚,你小时候追着我打时,我就还几下手。”
陈渺然用火钳夹了一截柴火,呵道:“你要是敢还手,说不定我就逃婚了。”
“逃婚是个力气活,不吃饭跑不动。”赵迢放下锅铲,低声道:“我去喊娘吃饭,你热个冷饭,顺便把菜端桌子上。”
“行,换我来。”
陈渺然把锅里的酥肉汤盛进碗里,从木甑子里倒出一些冷饭,沿着锅边放了一圈冷水,她盖上锅盖,往灶里加了一把易燃的柴火,随着火舌的踊跃,空气中传来米饭的焦香味。
赵母出了房门,望见桌上的热气腾腾的饭菜,她话中带刺:“水苗,我能吃上你做的一顿饭,那可太不容易了。”
“要不是赵迢请好了婚假,又带回办酒席的钱。说不定,你还得过两年才能嫁过来。”
陈渺然皮笑肉不笑道:“妈妈,多亏了赵迢,以后我们能天天一起吃饭。”
实则内心又把那群文化人骂了个狗血淋头,要不是他们没事找事做,她根本不用这么早结婚,也不用在别人家做饭。
吃完早饭,赵母借口操办婚礼太劳累,她脑壳有些昏,都看不清楚人,估计要在家里歇几天。
赵迢道:“娘,你先休息,中午自己做饭吃,我和小渺先去生产队了。”
接着,他跨起装开水的军用水壶,和陈渺然一起出了堂屋,往地里走去。
两人去了保管农具的地方,大概等了二十多分钟,生产队的人全部到齐,在队长和计分员的安排下,陈渺然和赵迢单独行动,负责收在村口大地的玉米。
计分员是赵迢的表哥,在带着大部队上山之前,他拍了拍表弟的肩膀,“二弟,你还有五六天坐火车回部队,你和媳妇刚刚新婚,表哥特意给你们创造相处的机会。”
“那块田地靠近一队,说不定还能和大表妹见面,你好好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。”
赵迢忙道谢,“多谢表哥,等我回部队了,以后小渺在生产队里,麻烦表哥照看一二。”
“二弟,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计分员看了看周围,委婉提醒道:“小渺在一队时,和北京来的知青走得有点近,幸亏你提前回来结婚了。否则,我们江岸村的村花,也不知道花落谁家。”
赵迢听懂了言外之意,马上维护道:“表哥,小渺奶奶和肖理外婆是旧识,肖理下放到江岸村进行劳动改造,作为故人之孙,陈家照看一二,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
陈渺然在前面等了很久,见赵迢一直在聊天,不耐道:“赵迢,今天早上说好了,你要挣十分工分,你再不去背苞谷,我们只能挣五分了。”
赵迢闻言,不好意思道:“表哥,小渺有一颗迫切劳动的心,我先去找她了。”
说完,赵迢提着背篓和镰刀,朝陈渺然小跑过去。
赵迢渐渐走近,陈渺然问道:“刚才你和他在聊什么呢,嘴角都没放下来过。”
“表哥说,只要我们两人单独把那块地的苞谷弄完,就给我们记十二分。”赵迢解释道。
“那走啊,快点。”
陈渺然顿时干劲十足,只想把十二分拿到手,工分越多,年末分到的粮食才越多。
赵迢十三岁下地挣工分时,陈渺然还没到年龄,陈渺然十四岁挣工分时,赵迢进部队当兵去了。
说起来,这是两人认识十八年以来,第一次搭配干活挣工分,陈渺然的心里有些别扭,未婚夫真变成了丈夫,她还有些不习惯。
两人站在村口的田地边,抬头一望,硕大的苞谷挂在头顶,同时叹道,这是一场硬仗。
夫妻俩在来的路上商量好了分工,当然是陈渺然单方面的决定,她负责剥苞谷穗,砍苞谷杆,赵迢负责背苞谷到晾晒的场坝。
从早上忙活到中午,两人午饭都来不及吃,主要是三队食堂修的远,一来一回浪费时间。
陈家父母去学校上课时,两人隔老远就看见了女儿和女婿的身影,陈母替陈父顶了两节课,让丈夫回家做午饭。
陈渺然用镰刀奋力砍着苞谷杆,肚子饿的发空。突然,她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,“小渺,快来吃饭了。”
陈渺然一愣,这道嗓音有点像她爸。随即,那道嗓音多了几分不悦,指责道:“哪个神人把我幺女安排在这里,这是要把她给整死啊。”
“爸爸,你怎么来了?”
陈渺然急忙从苞谷林里窜出来,头发上还沾了不少苞谷须,疑惑道:“你不是在学校上课吗?”
陈父举了举手里的竹篮,邀功道:“儿行千里母担忧,女背苞谷父心痛,小渺,我中午跑回家,给你拿来了你最爱吃的腊肉排骨,快放下镰刀,吃饱了再干活。”
陈渺然还没忘记那句话,反问道:“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,你还拿饭给我吃,不怕我回去把家淹了吗?”
“仙人诶,你赶紧吃饭吧。”陈父放下竹篮,无奈道:“我要是不说些歹话刺一刺你,你会安心和小迢领证?”
陈渺然以为自己看错了,她赶紧揉揉眼睛,差不多揉了两三回,又睁开眼睛来回打量,依旧不见橱柜的影子。
她以为赵母将厨房放在了灶房,便来灶房探探究竟,乌漆嘛黑的低矮房屋里,水缸旁边摆的还是原来的破橱柜。
陈渺然脸色顿时一垮,浑身上下散发着焦躁,一种独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动的飞扬浮躁。
赵迢刚刚喂完猪出来,他瞬间发觉了妻子的不对劲,赶紧问道:“小渺,你是不是饿了,我这就烧火做饭?”
“饿什么啊,气都气饱了。”
陈渺然没好气道:“我陪嫁的橱柜不见了,除了你妈的房间没找,其他地方我都找遍了。”
言外之意,你先去找找,如果真的找不到,我们再看如何掰扯。
正在这时,赵母走路的动静在坝子里响起,她发出尖冷指教的嗓音,“赵迢,怎么还不做晚饭,你们在三队食堂吃了饭,我可啥子都没吃。”
这一句话,让屋里的气氛势如彍弩。
赵迢深知陈渺然的脾气,他安抚似的逮住她的手腕,摇头示意她别说话,这件事情交给他处理。
他先解释没做晚饭的原因,“娘,我和小渺挣完工分,回了她家一趟,刚到家没多久。”
接着,他拿起火柴点燃灶台上的煤油灯,问道:“对了,你今天去哪里了?”
赵母似乎在放背篓,雄厚有力道:“这两天家里办酒席,你七舅家出了不少力气,趁着你在家挣工分,我特意送一些谢礼过去。”
赵母是隔壁村人,娘家姓蒋,她排行第四,上有三个姐姐,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
蒋老爷子向来重男轻女,在没生儿子之前,他特意收养了堂弟的儿子,继承香火。但生下小儿子后,蒋老爷子把养子重新还给堂弟,搞的两家关系紧张。
蒋老爷子将错就错,平时在路上看到了堂弟和侄儿,仗着自己有了亲儿子,连一声招呼都不打,直接抬起下巴走人。
而堂弟一家懒得计较,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处事原则,他们直接搬来了江岸村,恰好堂弟和赵迢爷爷是战友,两人有着战场上厮杀的交情,也有共同的讨嫌对象。
因此,两家绕过蒋老爷子一家,感情一向不错。比如今天给赵迢写十二分的计分员,就是蒋老爷子堂弟的孙子。
六个女儿陆续嫁人后,蒋老爷子变本加厉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,大到小孙子在医院的出生费用,小到买个油盐酱醋的钱,都让女儿们私底下凑钱。
要是六个女儿不出,就在村口骂人家忘恩负义,不忠不孝,还跑去女婿家里胡搅蛮缠,闹得各家鸡犬不宁,无论蒋老爷子提什么条件,全部一口应下,恨不得把人打发走。
赵迢从小到大深受其害,导致他对自己的亲外公和亲舅舅一家没多大耐心,他一边烧火做饭,一边不动声色的打听:“娘,你给七舅家送了什么,昨天剩了很多酥肉,怎么不抓一点过去?”
“抓了,我抓了好大一袋酥肉。”赵母沾沾自喜道:“你七舅家的碗橱坏了三四个月,平时拿饭菜不方便,我早上刚把家里的新碗橱背回去,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,都没赶上你七舅家的午饭,我都快饿死了。”
赵母一边说,一边闻着菜香来到灶房。
陈渺然本就忍着气,一听赵母供认不讳的话,猛得从木凳上窜起来,和赵母撞了个面对面,质问道:“你凭什么乱动我的嫁妆,那是我幺爷花了三个月做的!”
陈渺然带过来的所有木头嫁妆,全是幺爷亲自上山砍榆木,又慢慢把木材拖回家,制成木板,上墨涂漆,前前后后花了两年时间。
虽说儿媳妇是自己亲自看到大的,但赵母很不满意这个儿媳妇,一看她竟然敢对长辈大喊大叫,斥道:“陈渺然,你既然进了赵家的门,那你带进来的所有东西,都是我说了算。”
“我作为赵家的当家人,作为你的婆婆,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乱吼,亏你爹还是大学生,竟然连尊老爱幼都不教你。”
陈渺然立即反驳:“我陈渺然的东西,哪怕砸烂当柴火烧,也不会拿给好吃懒做的人家用。”
赵迢甩下锅铲,直接一个大跨步来到两人中间,以身高优势隔开了婆媳俩,随即把话头对准了赵母,强装镇静道:“娘,那是小渺带过来的嫁妆,你怎么能乱送人呢?”
“什么叫乱送人?你亲舅舅是外人吗?”赵母见儿子不帮自己,叫苦道:“赵文,你生的什么儿子哟,娶了媳妇就忘了妈,我就拿了一个碗橱送人,恶媳妇就想把我给杀了。”
“我的命好苦哦,丈夫是当兵的,儿子也是当兵的,父子俩都不把我放眼里。”
陈渺然想推开赵迢的手臂,但她力气小,根本推不动,冷笑道:“您看看家里的破碗烂柜子,到处是老鼠走过的痕迹,那个新碗橱放自家用不好吗?非要上赶着送给蒋家?”
赵母把灶台的陶碗一扔,瞬间摔成七八块碎片,振振有词道:“那是我亲爹和亲弟,我想让他们用上好东西,我有什么错?”
“陈渺然,你要是不想待在赵家,你就赶紧滚回去,我可不要你这种小里小气、斤斤计较的儿媳妇。”
按照陈渺然以往的脾性,肯定提脚就走,但她害怕和赵迢离婚后,陈家因为成分问题,会被别人逮着指骂。
她奶奶那么大年龄了,可经不得任何变动,她费力地吸着鼻子,向后退了几步,不服道:“算您赢了,您干脆把锅碗瓢盆都送给蒋家,让旁人都夸你的孝顺淑德。”
“这个日子,您想怎么过就怎么过,我都无所谓,大不了一起到处要饭吃。”
陈渺然说完这句话,转身而走。赵迢还没反应过来,便眼睁睁的看着妻子回了房间,屋里很快响起门锁声。
赵母继续煽风点火道:“老娘要屁饭,陈家拿你当眼珠子一样,我女儿也嫁给了你哥,要是我吃不起饭了,天天腻在你们陈家,你爸你妈吃什么饭,我就端什么菜。”
忽然,空气中传来一个巴掌声,打断了男知青的说话声,一个中年男人骂道:“曾牛,你要是想和我女儿好好过日子,就快给老子闭嘴。”
“爸,你为啥要打我?”
曾牛是从成都那边来的知青,十六岁上山下乡到江岸村,一来就是五六年,由于回城遥遥无期,再加上年龄大了,到了安家立业的年纪,去年夏天,他刚和村里的姑娘领了结婚证。
大庭广众之下,被农村里的老丈人扇了巴掌,曾牛顿感脸上火辣辣的,有种自尊被践踏的挫败感。
中年男人怒道:“当年闹大饥荒,要是没有陈家老人开仓放粮,江岸村的男女老少,早就饿死了,哪有你和我女儿结婚的份儿?”
中年男人口中的饥荒,是建国前西南闹的大饥荒,蝗虫过境,颗粒无收。
面对灾情,那时还是佃农的村民们最担心的事情,并非饿死,而是害怕交粮。
但陈奶奶直接免了那年的田租,还在族里祠堂里设了粥棚,单日男人领粮,双日女人来领粮,还在国民党镇压革命时,暗中支持了八路军不少粮食。
在特殊时期,陈家成分复杂且不正确,很少被拉去县里批斗,一是积累善事多,村里人或多或少都受了恩情;二是运气好,好笋歹笋对半长。
陈渺然奶奶的大哥,在长征途中牺牲,被追为革命烈士。陈渺然的大伯,在百团大战中牺牲,同样追为革命烈士。
陈渺然的父亲,在大学毕业后,在重庆入了国民党,同村族兄在自贡当裁缝,却被国民党揪出来,说他是共党分子,要被拉去枪毙。
那时候,陈渺然父亲刚好在自贡出公差,听说了族兄的事情,他跟长官主动要求押送族兄,想借着机会回家看看。
半夜,趁看押士兵疲惫之际,陈渺然父亲拿起板凳,将两位士兵砸得昏睡不醒,便拿起军刀割断了族兄的麻绳,和族兄先后跳了火车,两人相互搀扶着,一瘸一拐的回了江岸村。
陈渺然父亲救下的那位族兄,他早就加入了八路军,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带领手下的游击队取得多次胜利。1949年建国后,经全村村民选举,他被选为江岸村村长。
城里人头一次听说这些事情,脸上都有些羞愧难当。
李涛嚷嚷道:“村长,就算陈家是烈士家属,但还有着海外关系,但今天这一场教育,是民心所向。”
“是仅代表你们城里人的心,还是代表了我们江岸村村民的心?”
人群后面,慢慢走出一位少女,剪着齐耳短发,继续道:“陈渺然同志是我弟弟的未婚妻,我们赵家是赤农。”
“芸姐,你来了?”
眼前的少女名唤赵芸,她的龙凤胎弟弟赵迢,正是陈渺然的娃娃亲对象。而赵芸本人,也是陈远然的娃娃亲未婚妻。
赵家当年是从山东逃难来的,逃到江岸村时,全家只剩着三个红苕。陈渺然奶奶经历过战乱,本着帮急救难的家训,她给了赵家一处泥墙房落脚,命长工送了些粮食和锅碗过去,租了一些土地给赵家种,才让赵家度过了寒冬。
土地改革后,赵家分得了土地,和陈家感情非但没变淡,反而慢慢深厚,成为隔了两道山弯的近邻,一起帮衬着过日子。
1956年芒种,赵家得了一对龙凤胎,姐姐取名为赵芸,弟弟取名为赵迢。1958年端午,陈家也得了一对龙凤胎,哥哥取名为陈远然,妹妹取名为陈渺然。
四人年纪相仿,没上小学之前,就一起上山割猪草。上小学后,四人成了小学同学,经常结伴回家。
村长和赵父商量说道:“赵家是贫农,还是烈士家属,不如赵陈两家定一个娃娃亲。”
在多年情谊下,赵父满口答应。
近几年村里的知青越来越多,由于城里人很少干农活,他们天天借口腰痛脚痛干不动活,或者故意锄掉地里的菜苗,导致江岸村为数不多的教育大会,也会教育知青。
城里人为了转移战火,便天天盯着陈渺然一家不放,只要村民敢教育他们,他们就教育陈家。
赵芸孤身站在人群中央,据理力争道:“亏你们还是城里来的文化人,政府让你们上山下乡,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。”
“但你们干了什么事情,既不上山砍柴,也不下乡喂猪,天天盯着村里人不放,到底要不要脸?”
“我们不要脸?”
一位女知青挑了挑眉,阴阳怪气道:“赵芸,你护着未过门的弟媳妇,人家心里不一定有你的弟弟。保不齐,人家只是借着和赵迢的婚事,逃脱教育,只等时机成熟,她就进城享福去了。”
“李萱,你不要在这里大放厥词,血口喷人!”陈渺然在生产队时,无论她干什么农活,李萱永远在背后冷嘲热讽,她早就看不惯李萱了。
李萱继续道:“上次,我就看着你和肖理紧紧挨在一起,他偷偷给了你一包东西,你若是真心接受与赵迢的婚事,就不会和其他男人走那么近。”
“对了,肖理可是北京来的,将来他回了北京,前途光明。前段时间,你家还请肖理吃了一顿饭,肯定是帮着你和他私相授受。”
结婚第三天,陈渺然和赵迢挣完工分,抽空回陈家吃了顿晚饭,当做回门饭。
陈远然和赵芸也回了一趟赵家。
赵母看见出嫁不久的闺女,眼泪汪汪的就开始告状,说她的命比黄连还苦,新进门的媳妇不孝顺婆母,刚结婚的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。
她拿了一个多余的橱柜送人,陈渺然就哭着闹着不吃饭,赵迢为了哄人开心,就再也不寄钱给她花。
赵芸被赵母的话搞得糊里糊涂,难言道:“娘,阿远上门吃饭,你别说了,行不行?”
“为什么不能说,我没站在村口大声说,已经算给陈家脸面了。”
赵母见女儿不想搭理她,眼泪流的哗哗的,“常言道嫁出去的闺女,就不能管娘家的是是非非,赵芸诶,你才嫁过去三天,就忘记你亲娘了嘛?”
赵芸耳根子软,她想起自己在陈家也不受待见,心中的委屈宣泄而出,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,“娘,我也很想你。”
陈远然在旁边站着不是,坐着也不是,只好打圆场道:“娘,小渺要是犯了什么错,您告诉我,我待会儿就说她一顿。”
赵母听了这句话,如同拿到鸡毛令箭一般,她将橱柜争执一事全盘托出,还添油加醋的篡改了几句话。
说她出门送橱柜时,事先问过了儿媳妇的意见,但儿媳妇干完农活回来,不仅翻脸不认账,还骂她是贪便宜的老妖婆。
陈远然了解同胞妹妹的脾性,暗自下定决心,待会儿回家路上碰见妹妹,要和她好好聊聊,必须尊重长辈,不能对长辈恶语相向。
而在另一边,在陈家长辈热情款待下,陈渺然和赵迢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饭,无论长辈问她什么问题,她都回答:“都挺好的,婆婆拿我当亲女儿看待。”
赵迢寻了一个机会,把陈父和幺爷喊出去聊天,他拿出欠条,歉意道:“爸,幺爷,我娘没经过小渺同意,就拿了一件嫁妆送给了我亲舅舅,百善孝为先,我娘拉扯我们姐弟俩长大不容易。“
“母债子偿,天经地义。我把橱柜按照市场价折算成六十块,这里是二十块,至于剩余的四十块,等我发了工资,我再寄给您们。”
此话一出,陈父和幺爷的反应各不相同。
陈父把欠条推回去,“小赵,左右都是一家人了,还分这点钱算什么?”
“拿回去,赶紧拿回去。”陈父继续推辞道:“等你回到部队,赵家只剩亲家母和小渺相依为伴,你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,否则小渺要遭大罪了。”
幺爷心痛道:“我的乖孙女哦,她小时候不喜欢的拨浪鼓,宁愿放进灶房里一把火烧了,都不愿意送给她表姐。”
“小赵,不就一个小小的碗橱吗?我再做一个就行,没多大的事情。”
他拍了拍孙女婿的肩膀,又重新把欠条拿过来,“等你赔够了数,我再把碗橱送过去,记得提醒你娘,不要乱送东西出去,送给好人还有说头,要是送给蒋家人,确实太浪费了。”
赵迢见幺叔收下了欠条,继续提出自己的想法,“爸,我娘性子不好相处,等我离家归队了,要是家里方便的话,可以让小渺回来住吗?”
自从陈渺然出嫁后,他的傻三妹每晚都在闹,陈父如同看见了救星,应道:“方便,小渺的房间永远都在,你当女婿的都没意见,我们做父母的更是双手赞成。”
天色不早了,陈渺然和赵迢主动请辞,两人到祠堂门口时,刚好和各自的哥哥姐姐碰面。
陈渺然先喊了一声“芸姐”,这才对着陈远然喊了一声“哥哥”,陈远然就等着这一刻呢,他把陈渺然喊在一边,兄妹俩嘀嘀咕咕的说了半天,最后闹得不欢而散。
走在回家路上,赵迢见陈渺然魂不守舍的,温和打听道:“怎么啦,和你哥哥拌嘴了?”
陈渺然冷冷道:“与你无关,你别瞎打听。”
赵迢不敢再追问,便继续说些搞笑的事情,想让她重新露出笑容,却做了一番无用之功。
赵迢归队的日子很快就到,陈渺然提前和生产队告了假,两人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,一起坐大巴来到县城。
陈渺然似是感受到了离别,“赵迢,你回去......注意安全,别以为我们领证结婚了,你就不用写信了。”
“姑奶奶诶,我哪怕有十个胆子,也不敢不给你写信啊。”赵迢把人慢慢拥在怀里,不舍道:“我听村长说,明年村里要安电话,等电话安上了,我给你写信,也给你打电话,你可别嫌弃我烦。”
陈渺然点点头,“行,我愿意跑那五里地。”
村长家在村口的土公路上,赵迢家在半山腰,隔着蜿蜒不绝的山路,接个电话,差不多要跑三四十分钟。
火车出发的呜鸣声响起,陈渺然目送赵迢上了绿皮火车,火车上人山人海,赵迢费力地挤到自己的座位,他从狭窄的窗口探出头来,大声道:“陈渺然,你听我说!”
陈渺然的视线渐渐模糊,“你说吧,我听着。”
许是秋日的离别瑟意,让赵迢心脏里波涛汹涌的爱意,仿佛就要破膛而出,他喊道:“你等我回家,我们进城过日子。”
火车车轮滚滚向前,带走了逐渐模糊的黑色俊俏脸孔,陈渺然只看清了他的帽檐,她奋力地挥着手,任由失落在心底蔓延。
送走了赵迢,陈渺然回村种地挣工分,在幺爷出手相助下,赵家堪堪过了保底工分线,不用交钱补工分,也能分粮食。
除夕夜时,借着丰收粮食的喜意,赵母和陈渺然难得放下隔阂,婆媳俩做了几个好菜,痛痛快快地吃了一场,从1976年来到1977年。
小寒料峭,一番春意换年芳。
在正月春雨中,江岸村迎来新一轮的二十四节气,历经春雨、夏风和秋收后,全国人民迎来重大好消息,政府宣布恢复高考。
1977年 10月 21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发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》,标志着高考制度正式恢复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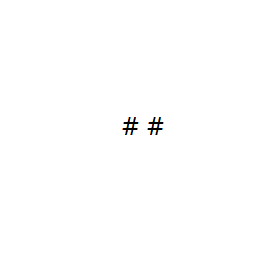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