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钱以亦唐慕青的女频言情小说《农村:开局替爸爸找妈妈结局+番外》,由网络作家“鄂佛歌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没想到班主任高老师又借此大做文章:“赵小禹同学做好事不留名,受到表彰仍能如此低调,丝毫不骄傲,这种精神难能可贵,值得同学们学习……”一夜之间,赵小禹仿佛成了众所瞩目的明星,浑身金光闪耀,弥漫着伟大的人性光辉。最令赵小禹激动的是,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,由佩戴着三道杠肩章的大队长,“优秀少先队员”许清涯为他系上红领巾。接下来却出现了尴尬的一幕:许清涯忘了红领巾的系法,尝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,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,她自己也笑得直跺脚。眼看严肃的表彰大会搞成了喜剧大会,高老师及时过来解围,喊了许清涯一句:“都二年级了,咋还这么笨呢?”许清涯爱笑又笨,削铅笔一项简单的工作,她学了一个多月才学会,但还是免不了要割到手,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她是个“...
《农村:开局替爸爸找妈妈结局+番外》精彩片段
没想到班主任高老师又借此大做文章:“赵小禹同学做好事不留名,受到表彰仍能如此低调,丝毫不骄傲,这种精神难能可贵,值得同学们学习……”
一夜之间,赵小禹仿佛成了众所瞩目的明星,浑身金光闪耀,弥漫着伟大的人性光辉。
最令赵小禹激动的是,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,由佩戴着三道杠肩章的大队长,“优秀少先队员”许清涯为他系上红领巾。
接下来却出现了尴尬的一幕:许清涯忘了红领巾的系法,尝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,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,她自己也笑得直跺脚。
眼看严肃的表彰大会搞成了喜剧大会,高老师及时过来解围,喊了许清涯一句:“都二年级了,咋还这么笨呢?”
许清涯爱笑又笨,削铅笔一项简单的工作,她学了一个多月才学会,但还是免不了要割到手,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她是个“傻子”,然而她学习却是那么好。
凭借着好学习,她当上了学习委员,成为建设小学第一批少先队员,还当上了大队长。
高老师替赵小禹系上了红领巾,带领他宣了誓。
其后,赵小禹的“光荣事迹”被老师们书写在教室外墙的露天黑板上,接受着同学们的观瞻,接受着风吹日晒。
赵小禹本来野惯了,课间总是到处乱跑,但自从见义勇为事件后,他就乖多了,下课后就待在教室里;放学后就拉着金海匆匆回家,因为他一见到人,尤其是高年级的那些学生,他们总会喊他“英雄”,这让他十分尴尬。
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,他总觉得他们口里的英雄,不是一个褒义词,带着一点起哄和调侃的意味。
他埋怨金海:“你随便说两句就行了,干嘛要说得那么肉麻?”
金海说:“是高老师教我那么说的,我背了两天才背会。”
一场秋雨过后,黑板上的彩色粉笔字模糊成无法辨认的一团,赵小禹头上的光环也褪去了颜色,不再鲜艳,他不再鹤立鸡群,恢复到一名普通小学生的身份。
然而又有一件事,在班级乃至校园里掀起了波澜。
这天放学,赵小禹和金海去了高老师的办公室。
两人各自将一张请假条放在高老师的桌子上,赵小禹说:“我们明天请一天假。”
高老师疑惑地看了两人一眼,拿起两张请假条依次看。
赵小禹的请假理由是:我爸结婚。
金海的请假理由是:我妈结婚。
学校对于学生请事假控制得较为严格,必须要写清楚具体的事,不像请病假那样容易,而且一般的事由不予批准,必须是非请假不可的理由才行。
在老师们看来,一帮小屁孩,能有什么屁事值得请假?
赵小禹没妈,金海没爸,这在学校里不是秘密,所以高老师略微思索了一下,便明白了问题的核心:“不会是你爸和你妈结婚吧?”
“就是的。”赵小禹说。
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好几个老师,一齐把目光投向两人,接着便叽叽咕咕地笑了起来,笑得两人无地自容,尤其是金海,连头也不敢抬。
高老师也笑了,说:“好事,准了!”
这事很快在学校里传了开来。
那年月,重组家庭本来就具有热点,而像赵小禹和金海这样的特殊关系就更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。
两人是同班同学,一个是班长,一个是第一;一个不仅每天背着另一个过担担,还救了他一命,原来是亲如兄弟,现在成了亲兄弟。
说着,他解开衣扣,给高老师展示身上的几处伤疤。
“这都是子弹打的!我九死一生,把敌人赶跑了,现在却连自己的孙子都保护不了!”
高老师面色凄然,说:“难为你们了,但是大爷,我相信,时代在进步,好的东西会越来越多,坏的东西会越来越少,总有一天,好人能得好报,坏人能受到惩罚。”
饭吃完了,家访也进行完了,高老师要走,说:“赵小禹,你带我去一趟武飞龙家。”
赵大顺立刻警觉起来:“你去他家干什么?”
高老师说:“武飞龙的姐姐武玉凤不是退学了吗?今天我说我要去新建队家访,武玉凤她们班的班主任让我给武玉凤捎句话,劝她回去继续上学,犯了错误,就应该受到惩罚,但上学是她的权利,没有人能剥夺。她马上要上初中了,现在退学,可惜了,听说她的学习还不错,别一时冲动,毁了前途。”
赵大顺问:“武玉凤犯了什么错误?”
高老师看向赵小禹,见他低头不语,神色闪烁,料到他没把学校发生的事告诉家人,便说:“没什么大事,老师批评了她几句,她就不念了。”
赵小禹领着高老师走在村路上,向他介绍着村里的情况。
高老师很是善解人意,她知道武家和赵家矛盾颇深,如果赵小禹领她去武家,恐引起误会,便说:“你给我指一下他家就行,你不用过去了。”
走了一会儿,望见武家,赵小禹便指给高老师,自己返回家去了。
他天不怕地不怕,但还是怕武家。
那天下午,高老师去武家具体说了什么话,做了什么事,赵小禹不得而知,他只知道,就在第二天,武家的二媳妇王翠萍死了,吊死在自家院门外路旁的一棵大树上。
那条路,是新建队的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。
冬天夜长,天还没亮透,有些人家就点起了蜡烛,给上学的孩子做早饭。
一阵尖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祥和。
赵小禹和金海经过武家门前的那条路时,见有几个学生聚集在那里,一个个面如土色,听他们说,他们亲眼目睹了武家二媳妇王翠萍的尸体吊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,身体拉得又细又长,那条断腿明显比另一条腿长一截。
赵小禹并不确切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只是马上联想到昨天高老师的家访。
农村事少,一旦有件大事,马上就传遍十里八乡。
王翠萍上吊这事,当天就在建设小学传得沸沸扬扬。
上早自习时,高老师把赵小禹叫出教室,问他:“武飞龙家里,那件事,是真的?”
赵小禹点点头:“他二嫂,上吊死了。”
高老师哦了一声,脸色惨白,跌跌撞撞地走了。
农村人爱热闹,丧事都是喜事,每逢谁家死了人,人们纷纷前往,向主家问候,议论一下死者的生平,看看纸火的规格,鉴赏一下鼓匠的水准,抽几支免费的好烟,喝几碗免费的茶水,孩子们也爱去凑热闹,胸口别着一块用来辟邪的红布条,像过年一样高兴。
但那是正常死亡的,所谓喜丧。
而对于非正常死亡的,尤其是像王翠萍这样年轻的,人们则无此雅兴,反而还觉得害怕。
老年人传言,阳寿未终死亡的人,投不了胎,转不了世,一直游荡在阳间寻找替身,如果有人走夜路时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,千万别回头,别应声,否则就会接了鬼音,必死无疑。
剩下的一条红鲤鱼,赵小禹也没有拿回家。
他跑到孙桂香家的院门外。
毫无意外,从大门墩上伸出两根椽子横在那里。
椽子自然挡不住赵小禹,但他不敢进去。
黑狗许是听到了脚步声,许是闻到了鱼的腥味,汪汪地从院里跑了出来,扑向赵小禹。
赵小禹喊了一声,黑狗不退,反而叫嚣得更凶猛了,露着尖牙利齿。
狗从来都是最懂人类的,家里无论来了什么人,哪怕它知道是谁,但在主人确认之前,它都要将其拒之门外。
赵小禹后退了几步,黑狗追了上来,好在只是叫,并不下口。
这也是狗的可贵之处,不虚张声势不足以吓退来访者,但真要下口咬人,则会给主人添麻烦。
这时,听到“啾啾”两声,黑狗得到命令,立刻停止了叫嚣,转身回到大门口,爬伏在站在两根椽子后面的金海脚下,嗷呜嗷呜地撒着娇,摇着尾巴。
看到金海,赵小禹笑着跑过去,问:“你妈呢?”
金海回头努了努了嘴:“在家。”
他看到了赵小禹手里的鱼,眼睛中闪出惊奇的光芒。
“哪来这么大的鱼?”
“我抓的!”赵小禹得意地炫耀着,空着的一只手摸了摸沾在头发上的干泥块,仿佛那是他的荣耀,像爷爷身上的枪伤,像士兵胸前的勋章。
他把鱼往高提了提,“送给你,你拿回去,让你妈给你炖着吃,这鱼刺不多,肉大。”
“真的要送给我吗?”金海有点不敢相信。
“真的啊,快拿着吧!”
金海高兴地接过鱼,双手提着菅草,把鱼提到眼前,爱不释手地端详着。
“咱们一起去上学吧。”赵小禹开始替许清涯招募学生。
“我妈让我明年上。”金海说。
他比赵小禹和许清涯小一岁,还不到上学的年纪。
全村共十一个小队的孩子,拼凑出一个小学,建在村部,距离新建队七八里路,所以那里的孩子上学普遍都晚。
因为离家远,学校只能实行“一放学”制度,即:中午不回家,一早去了学校,下午两三点一次性放学。
午饭靠自带的干粮解决,不带干粮的就得饿着。
那时的孩子,都有超强的忍饿能力。
什么午休,不存在的。
这样的制度也达到了家长们“压榨”孩子劳动力的目的,放学回家后,还要去地里干活。
“不是上那个学,是上许清涯的学。”赵小禹解释道,“许清涯现在当老师了,要教我们这些还没上学的孩子念aoe,算算术。不用去学校,就在村里。”
“许清涯是老师?”金海不解,“她不是刚上学吗?”
“啊呀,跟你说不清,我明天过来找你,咱们要准备一个书包,一个本子,一支笔……”
赵小禹忽然住了口,他看到孙桂香从正屋出来,向这边走过来。
“金海,谁呀?”她说着,看到了赵小禹,脸立刻拉下来,走到大门口,满怀敌意地看着赵小禹,“你来干什么?不是让你别再骚扰我家金海了吗?”
“妈妈,赵小禹给咱们家送的鱼。”金海把那条鱼提起来,可怜巴巴地说。
显然,他很想把它据为己有。
孙桂香瞅了一眼那鱼,脸上的神色并没有缓和,问赵小禹:“你给我们家送鱼干什么?”
赵小禹挠了挠头:“你送给我家的肉和虹豆真香,我送一条鱼还给你家。”
想了想,又补充了一句:“这是我抓的鱼,我爸和我爷爷不知道。”
孙桂香的眼皮子抬高一些,旋即又耷拉了下来,对金海说:“把鱼给他。”
金海只得把鱼从两根椽子上递出来。
赵小禹却没接,转身跑了。
不知是不是那条鱼发挥了作用,孙桂香竟然不再阻止金海和赵小禹来往了,也允许赵小禹去她家了,尽管她每次看到他时,还是很不友好。
许清涯的“学校”很快办了起来,就在她家的院子里。
她爸妈不像村里人一样讨厌赵小禹,也很支持她的“办学事业”。
她家有三个孩子,许清涯还有两个哥哥。
大哥已经上了初中,在公社住校。
二哥也已经上四年级了,每天放学回家,都要跟着爸妈去地里干活。
做为最小的孩子,爸妈很宠许清涯,既然她想“办学”,那就办吧。
孩子嘛,爱玩就让她玩去。
她爸甚至还给她用墨汁粉刷了一块小黑板,钉在院墙一角。
许清涯在土地上画了一个四方框,代表教室。
她拿着从学校带回来的粉笔,装模作样地在黑板上书写“aoe”和“1+1=2”。
她的学生只有两个,赵小禹和金海。
两人没有桌子,搬来土坯充当凳子,正襟危坐着,倒也像模像样。
书包是用塑料布缝的,本子是用废纸钉的;可怜的赵小禹,连支笔都没有,找了块炭疙瘩磨尖了当笔用,往往把两只手染得黑亮黑亮的,晚上睡觉时又染在被子上。
不过这个游戏没持续多久,问题出在许清涯身上。
她“三令五申”让赵小禹和金海不能违反课堂纪律,自己却经常开小差,讲着讲着就觉得没意思了,她本来也没学会多少东西。
主要是,这两个学生太听话了,比学校那帮学生都守纪律;她让他们算算术,两人竟然都能算对,她想教训一下他们都找不到理由,一点也体会不到当老师的乐趣。
金海本来胆小,经常被村里同龄的女生欺负哭,自然不敢违拗“许老师”。
赵小禹本来胆大包天,但在许清涯的课堂上,却乖巧得像个小猫一样。
许清清往往把教鞭在黑板上啪啪地抽几下,搜肠刮肚地想发表一通“重要讲话”,最后却只是兴叶索然地说一句:“下课!”
或者说:“放学!”
或者说:“咱们还是踢毽子吧。”
当了几天老师,许清涯最终发现,还是当学生快乐。
大规模的秋收时节到了,赵小禹就开始忙了,许清涯的学校也就解散了。
但赵小禹仍叫许清涯“许老师”。
农村人的活都是赶在一起的,割葵花,掰玉米,挖籽瓜、收白菜、起蔓菁;然后再打葵花,搓玉米,冬储白菜和蔓菁……干不完的活。
在秋风萧瑟中,赵小禹消磨着他的童年时光。
“说!”赵大顺看了一眼赵小禹,收起了笑容。
他对这个用两千斤小麦换来的儿子还是比较了解的,他平时说话口无遮拦,每当犹犹豫豫时,说出来的话必不中听。
当然,他口无遮拦说出来的话也不中听,不过那只是脏话而已,赵大顺不在乎。
“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呀。”赵小禹胆怯地说。
“说吧,爸爸不生气。”赵大顺惬意地揉着肚子。
他心情好的时候,就给儿子当爸爸;心情不好的时候,则给儿子当老子,虽然意思一样,但给赵小禹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很大的区别。
他抚摸了一下儿子的头,见儿子正要开口,忽然又想起一事:“就是不准提孙寡妇!”
赵小禹缩了一下脖颈,只能把滑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:“我瞌睡了。”
“瞌睡去睡啊,谁拦着你了?”赵大顺竖起了眉毛,还是有点生气了,“自己铺床!这么大个人了,还等我吗?”
赵小禹噢了一声,到炕角将自己的被褥拉下来,脱下衣裤睡了。
赵家有三间房,是西北人情有独钟的“一进两开”的格局。
西房有一盘火炕,几乎占据了一半的面积,赵家祖孙三代,都在这盘火炕上睡觉。
火炕连着炕炉,冬春秋三季,就在炕炉做饭。
炕上铺着人造革油布,摆着炕桌,既是吃饭的饭桌,又是待客的茶桌。
“米酒油馍木炭火,团团围定炕上坐”,说的就是这样的场景。
不过这里的人很少喝米酒,他们更爱喝白酒,五十六度的高梁白是他们的最爱。
中间一间屋基本空着,只在夏天炎热的时候,炕烧得人受不了,便倒在这屋做饭。
西屋充当凉房用,堆满了各种粮食和杂物。
赵家不仅没有女人,连凉房、粮仓、厕所、院墙这类基本的生活设施都没有。
赵天尧年轻的时候,懒得盖这些;等到他觉得这些有用的时候,已经老得盖不动了。
他不止一次让赵大顺起道院墙,齐齐整整才像个人家,女人们也愿意来窜门。赵大顺却总是一拖再拖,还振振有词:“没院墙好,省得扫院!”
赵天尧后来就懒得管了:“噢,那你自己看吧,反正我用不着老婆。”
倒是有个猪圈,也破破烂烂的,猪跑过好几回,父子俩经常满村子撵猪。
那头为他家立过汗马功劳的老骡子也没个像样的住所,只是栽了四根木棍,上面搭了一个茅草顶。
这样的家庭,诞生出两个老光棍,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赵天尧今天已73岁,是标准的老光棍。
赵大顺虽然只有38岁,但在那个年代,叫他老光棍也不算冤枉他,尽管他很讨厌这个身份。
赵小禹平时野惯了,不到眼皮子抬不起来的时候不睡觉,今天睡得早,半天睡不着,在被子里翻来覆去,抠抠搜搜的。
鼓胀的肚子让他难受,让他忘了吃肉时的享受,这时他觉得不该接受孙桂香的油和肉,主要是爸爸不接受孙桂香,这让他很难办。
明天去给孙桂香还钵子的时候,该怎么说?
继续骗她?
如果她得知自己骗了她,会怎么对付他?让他把肉吐出来?
吐是吐不出来了,倒是能拉出来。
不过他挺喜欢孙桂香的,挺愿意认她这个妈,满村子的人都讨厌他,嫌他野,嫌他不懂礼貌,嫌他满口脏话,嫌他偷吃他们的零碎,只有孙桂香给他肉吃,当然这是沾了父亲的光。
零碎是此地人对蔬菜的统称,诸如黄瓜、西红柿、虹豆、茄子、青椒、甘蓝等
此地人以种地为生,主要种小麦、玉米、葵花、籽瓜这些,有的是粮食作物,有的是经济作物,除了留下自家人吃的,剩下的卖给二道贩子。
讲究点的人家,还会种糖菜,用来熬糖;也有的种胡麻,用来榨油;还有种西瓜的,除了能满足自家人的口腹之欲外,还能卖钱和换粮食。
不管是讲究的人家,还是不讲究的人家,每家都会种零碎。
只需二分地就足够,每样种一两行,就是种起来比较麻烦,有的要压蔓,有的要搭架,有的要掐头,有的要配蕊,松土、锄草这些都需要精耕细作,一般都是女人干的活计。
贫穷的农村人总觉得,自己种着地,连新鲜蔬菜都吃不上,那就是一个笑话。
没错,这个笑话就是说赵家,赵家就从来没种过零碎,嫌麻烦,只是在夏天收了小麦后,淌过水,犁完地,在上面撒些白菜籽和蔓菁籽。
对于此地人来说,白菜只在冬天腌酸菜用,蔓菁是用来喂猪的。
赵小禹闲不住,冬天在村里疯跑,哪里热闹往哪里凑;夏天则在田野里疯跑,却是哪里人少往哪里钻,悄悄地踅摸到别人家的零碎地里,望望左右无人,飞快地摘几个黄瓜或柿子,然后躲在葵花林里饱餐一顿。
他也不想作贼的,实在是那些五颜六色的蔬菜太招人了,也怪那两个老光棍太懒。
孙桂香家也种着零碎,赵小禹也偷吃过。
孙桂香抓住过他一回,把他拎到赵大顺面前,他自然免不了受一顿捶打。
孙桂香家的零碎比别家的都好,西红杮更大更红,黄瓜更绿更长,哈蜜瓜更香更甜,虹豆结得像珠帘,茄子长得像牛轭,青椒大得像灯笼……
她家不仅种零碎,还养鸡,每天都有鸡蛋吃。
村里养鸡的人家不多,不知是那时的鸡难养,还是那里的人不会养,要么孵不出来,要么长不大就病死了。
可怜的赵小禹,连鸡蛋是什么味都没尝过。
如果她是我妈就好了。赵小禹不禁这么想。
孩子的心事有一阵没一阵,赵小禹乱想了一阵,在油灯摇曳的光亮下,渐渐睡着了,隐约听到爷爷和爸爸还在议论着那盆吃剩的白菜和土豆。
“半盆油糊糊,糟蹋了吧。”
“没事,秋凉了,能放住,够明天吃了。”
“明天再切点白菜中和一下,不然油太大。”
“那明天又吃不完了。”
“那就放在后天,再切点白菜,再中和一下,肥油辣水能吃个半月二十天。”
“嗯,有道理!”
……
熟睡中的赵小禹被腹内一阵剧烈的绞痛惊醒了,他捂着肚子坐起来,看见炕桌上的油灯亮着,爷爷和爸爸却都不在了,被子扯在一边。
但他顾不上想这些了,肚子里翻江倒海,已刻不容缓。
他披了件衣服,跳下炕,趿拉上鞋,跑了出去。
当当——当当——
下课了。
学生们蜂拥而出。
许清涯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树荫下的赵小禹,蹦蹦跳跳地跑过去,蹲在他面前。
“你又来了?”
“嗯。”赵小禹激动地把那三块高粱软糖掏出来,“给你吃糖,我今天给人寄信,人家多给了我一毛二分钱,我买了三块糖。”
许清涯笑着摇摇头:“我不吃,我家糖可多呢!我妈说,我如果再吃糖,牙就要全掉光了,就成了没牙老太太了。”
“吃吧,老太太是因为老才掉牙,又不是吃糖吃的。我爷爷倒从来不吃糖,现在用的是假牙。”
赵小禹把两块糖塞进许清涯手里,自己拿了一块,剥去包装纸,放进嘴里。
“甜不?”赵小禹问,“我还是觉得那天的糖甜。”
“哪天的?”许清涯也将一块糖塞进嘴里。
“就你送给我家的那七块糖。”
“那个甜吗?那是因为你当时正疼着呢,就觉得糖很甜!”许清涯发动牙齿嚼着软糖,“那个糖一点也不甜,还有点酸,嚼着吃硌得牙疼,化着吃酸得牙发麻。还是这种糖好吃,软软的,黏黏的,甜甜的。”
两人吃了糖,赵小禹又将一颗西红柿和一根黄瓜给了许清涯。
当当当——当当当——
上课了。
许清涯把黄瓜和西红柿揣进衣服里,跑回了教室。
赵小禹一手拿着黄瓜,一手拿着西红柿,吃一口绿的,再吃一口红的,美滋滋地往回走。
回到村里,看见王翠萍正抱着孩子站在上午她给赵小禹信的那个地方。
赵小禹走过去。
“寄出去了吗?”
“寄出去了。”
“是亲手交给邮递员的吗?”
“是。”赵小禹不想说得太多,他觉得只要贴上邮票,就没问题了,“我亲眼看见,他撕了一张邮票,贴在信封背面,然后收起了。”
不过这个“他”,不是邮递员,而是秦富忠。
“好,好,太好了!”王翠萍因为激动,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一抹红润,眼眶中闪闪发亮。
然后她抱着孩子转身走了,走了几步,回头又说:“小禹,你真是个好孩子!”
望着她有点跌跌撞撞的脚步,赵小禹不禁奇怪,叶春梅说他是个好孩子,是因为他放了她,王翠萍为什么也说他是个好孩子呢?
莫非,自己真的是个好孩子吗?
想起那一顿毒打,他本能地缩了缩脖颈,还是做个坏孩子吧。
当晚,住在武家周围的村民都听到武家院里有个女人嚎叫了一夜,伴随着男人的打骂声。
天刚亮,赵家祖孙三代还没起床,听到有人在外面重重地踹门。
“赵小禹,你给老子出来!”
“快开门,不然老子要砸门了!”
“今天非剁了你这个小王八蛋不可!”
三人一惊坐起,赵天尧和赵大顺狐疑地望着迷迷糊糊的赵小禹,问道:“你又干什么坏事了?”
赵小禹茫然地摇摇头:“什么坏事也没干。”
外面的人开始砸门,用上了工具。
赵天尧叫道:“等等,正在穿衣裳呢!”
他胡乱地穿上衣裤,过去开了门,一块门板已被砸破了,门头的玻璃也被震了下来。
好在那个年代的门都是实木的,虽不美观,却很结实,门轴和里面的木栓很坚固。
武家老的小的,男的女的,将近二十口人站在门口,黑压压的一片,手里都提着工具,有宰杀猪羊的屠刀,有切菜的菜刀,有刨地的䦆头,有割麦子的镰刀,甚至还有铡草刀……
一个个气势汹汹,杀气腾腾,叫嚣着要杀了赵小禹。
赵大顺也出去了,看到这阵仗,吓得心惊肉跳,两股战战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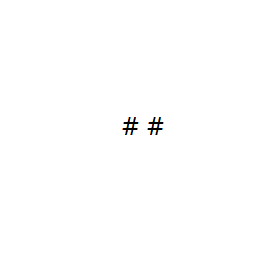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