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长海建新的其他类型小说《倒斗全文》,由网络作家“平川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“你为什么会去盗墓?”最初的时候,每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,我的回答就一个字——穷!直到经历长时间的改造后,我认识到:贫穷永远不能当做犯罪的借口,说到底,还是自己控制不住心中那份贪念。万幸的是,我没被彻底抛弃。哪怕出来时都快奔五了,可总算是洗心革面,有机会从头开始。户口恢复后,我在老家开了间小店卖茶叶。赚的不多,只图个本分踏实,平时喝喝茶、遛遛狗,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平静下来。不过最近我偶然发现,有个以前的同行,竟把当年的一些事情写了出来。老实说,我没他那么有本事,但受他启发,就也想聊聊自己的故事。一方面,算是反思一下曾经的过错;另一方面,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,告诫现在的年轻人:好好学习,奉公守法,千万不能走到犯罪的道路上......事情...
《倒斗全文》精彩片段
“你为什么会去盗墓?”
最初的时候,每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,我的回答就一个字——穷!
直到经历长时间的改造后,我认识到:
贫穷永远不能当做犯罪的借口,说到底,还是自己控制不住心中那份贪念。
万幸的是,我没被彻底抛弃。
哪怕出来时都快奔五了,可总算是洗心革面,有机会从头开始。
户口恢复后,我在老家开了间小店卖茶叶。
赚的不多,只图个本分踏实,平时喝喝茶、遛遛狗,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平静下来。
不过最近我偶然发现,有个以前的同行,竟把当年的一些事情写了出来。
老实说,我没他那么有本事,但受他启发,就也想聊聊自己的故事。
一方面,算是反思一下曾经的过错;
另一方面,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,告诫现在的年轻人:好好学习,奉公守法,千万不能走到犯罪的道路上......
事情要从我的家乡伊春说起。
由于挨着“老大哥”,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这里的“边贸生意”就异常繁盛。
在那个号称“一车西瓜换一辆坦克”的时代,为求暴富,好些人不远万里,带着各式各样的货物来到这里,只为了过去捞一笔。
本地人就更甭说了。
尤其农村,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干,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。
所以幼年时期,我生活很富足。
衣服多,玩具多,零食多......大部分都是进口的。
可也正是这个原因,导致我对父母的印象不怎么深刻。
记忆中,他们总是走了回、回了走......
一年到头算上春节,在家里待的时间,甚至都不超过一个月。
但我五岁那年,他们走了,却再也没回来。
我当时小,不明白“被黑了”究竟是个啥意思,还是听到奶奶哭着说,我再也吃不上他们带回来的光头饼和大头娃娃巧克力后,我才跟着,哇哇大哭起来。
那段时间,同样的事儿发生在不少家庭里。
然而这本就是见不得光的勾当,人们纵使不甘,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。
直到几年后,去那边的列车上,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案,再加上“旧双轨制”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,这条火 热了十几年的发财之路,才随之销声匿迹。
好在那时候,爷爷奶奶都还年轻。
家里有地,有父母留下的部分积蓄,生活质量纵使下降,也不至于饿肚子。
有人说:没爹妈的孩子会自卑。
我一度认为这话就是扯淡。
毕竟我们这群没爹妈的孩子,个个都很社牛。
嗯…确切说是村儿牛!
谁敢说我们自卑,我们就让他知道,什么叫做自闭。
尤其是那群有爹妈的。
不想自闭,就打到你自闭。
你要敢躲家里不出来,就砸你家玻璃、堵你家烟囱,让你全家连房子都跟着自闭!
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大家逐渐都意识到:这世上,远有比自卑要可怕的事情。
更可怕的是,你没爹没妈,就只能独自去承受这种可怕。
那年冬天,爷爷被查出了肝癌。
村儿里长大的孩子应该都明白,那个年代不光是医疗条件落后,更在于人们没有病患意识。
身体不舒服,一般都靠廉价的去痛片、安乃近,亦或某些不知从哪打听来的偏方扛着。
直到扛不住了,才会去正规医院检查。
基本上,确诊就意味着晚期。
可就算放弃治疗,就算只做些检查、买点止疼续命的药品,仍是大部分家庭难以承受的。
短短一个月,看病就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。
可爷爷,依旧没能熬过年关。
在腊月初十的寒夜里,他老人家,撒手人寰。
很多人印象中,那年春节都显得格外喜庆,但在我家,却是最窘迫的一段时光。
那些天里,我和奶奶每天都是两顿稀不溜丢的苞米渣粥。
为了省电,一到天黑灯都不点。
得亏是需要守孝,不然日子紧吧的,甚至舍不得花五毛钱去买一尺红纸,写副春联......
节俭始终不是办法。
没钱,就意味着迟早遇上各种难题。
眼瞅着,我快开学了。
那年除了学杂费,还有体检费和报名费,加起来,整整一百八十五块。
表面上奶奶没说什么,但到夜深时,她偶尔会坐起来,撩开窗帘,望着柴禾棚子发呆。
我知道奶奶的打算。
柴禾棚里,有她的寿材。
上好的红松木,是父母还在的时候为她置下的。
当时,我看着奶奶佝偻的背影,心都碎了。
为了让奶奶不再动这念头,我就骗她,骗她说学校知道咱家困难,费用可以先欠着,收了秋再交......
那年头儿在农村,几乎每次开学,都有人因为交不上学费被撵回家拿钱。
这次,轮到了我。
我知道回家的结果,就独自在村口一堆苞米秸秆里,坐了整整一天。
无论如何,我也不会让奶奶卖寿材供我上学。
我沈平川,再穷,也不缺这二两骨气!
爷爷走了,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,是家里的顶梁柱,不该也不能再让奶奶,为我 操心受累了。
事隔多年,如今回想起来,倒也说不上什么痛苦,但那天,的确是我这辈子最孤独、最漫长的一天。
太阳落山后,看着昏暗的山野,我暗暗发誓:
一定!要有钱!
一定要在奶奶身子骨,还硬朗的时候,成为有钱人!
奶奶她早晚也会有那么一天的。
真到了那天,我绝不让她像爷爷那样,躺在炕上等死!!
年少无知。
这种念头一旦出现,就会像开了春的野草一样疯长,再不受任何约束。
我几乎没有犹豫就下定了决心:想赚钱,赚快钱,就得走捷径!
而那时能带我走上捷径的,只有一个人——同村村民王长海。
他的捷径,是“倒斗”。
凌晨一点四十分,我们撬开了棺床正中间的一块石条。
周伶猜的不错,下面是空的。
当我们搬开石条,一个黑漆小木箱,便赫然出现在三把头灯的辉映之下!
由于石棺和棺床中间仅四十公分,所以我们当时都是趴着钻进来的,换句话说,如果这时候石棺落下来,我们都得被砸成肉饼。
“卧槽,真特么沉啊!”
长海叔一下没搬动,正准备再试,却被周伶拦住。
“不要搬,平川你来,直接把锁砸开!”
小木箱锁头很细,我一锤就搞定了,但因为闭合的太久,我用了好大的劲儿才掰开。
时隔多年,接下来的一幕仍令我记忆犹新。
伴着嘎吱嘎吱的响动,一抹柔和的光泽,从缝隙中乍现,而后随箱盖开启,一点点扩大,直至完全铺开,呈现在我们眼前......
是银锭。
所以周伶不让长海叔继续搬。
否则一旦箱子突然垮掉,产生磕碰,品相就会下降。
我第一次见古代银锭,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
银锭颜色偏灰,表面比较粗糙,如果从侧面看,形状确实有点类似电视上的银元宝,但没有中间那个凸 起,是平的,而且从平面中心开始,还有一圈圈水波一样的纹路扩散到边界。
此外,看着看着,我就明白了古代为什么会有“雪花银”的说法,因为随着光线的偏转,银锭表面,真的会显现出零星类似雪花的反光点。
周伶说这种银锭叫“十两束腰锭”,在明代,一锭这样的银子,就可以买两个丫鬟。
我有些吃惊,拿起来一个,感觉也就比鸡蛋大点,不过很压手。
银锭底部摸起来很粗糙,我翻过来一看,发现是一层蜂窝状的小孔,给人感觉不太舒适。
“诶?这是啥色儿?”
“卧槽伶姐!这不是假的吧?”
之所以这么问,是因为我仔细一看,发现那层蜂窝小孔表面,有一种淡淡的彩色。
就有点像那种电焊过后,留在金属表面的色泽。
周伶抬眼一瞟便道:“这叫五彩包浆,要长期稳定的氧化环境才能形成,一般只有窖藏能出,有这种颜色,不仅不是假的,反而更值钱!”
“哦哦,原来是这样。”我半懂不懂的点了点头,心说这都是知识,我得记住。
经过清点,银锭总共一百枚,都是十两束腰锭,其中两个有字,内容是“成化十三年,济南府徵,银匠丁昭”。
周伶说明代太监虽然不差钱,但很难攒下这种成箱的制式官锭。
所以,这大概率是老太监退养时,王府赏赐的安家费。
而手札记述,修墓是正德六年,这个时候老太监还活着,如果他是成化十三年退养,就说明退养之后,这人少说又活了三十多年。
看着一地的银锭,周伶感慨道:“千两赏银,难怪这老太监敢越制啊!”
当时没明白她的意思,因为小时候看电视里,动不动就赏金千两什么的,感觉似乎不多。
后来我才知道,那都不对。
在明代,除去战场之类的特殊情况,日常生活中,赏银千两这种行为,基本只有皇帝、皇后以及个别受宠的亲王才能做。
其他人即便给得起,也不能超过这个标准。
这虽然没有明确规定,但你想想,皇帝平常才给一千两,你却给一万两,那你指定是不想混了......
收好银锭,我们从新垫砖准备开棺。
为了加快速度,周伶叫建新哥也下来了,三个人快马加鞭,放好砖后便叮叮当当开始猛凿。
其间周伶也没闲着,用小刀修起了木楔子,这是开石棺用的。
记住,电视上那种手推石棺的画面都是假的。
别说石棺,木棺一个人想推开都很费劲,就比如我爷爷的棺材盖,要三个成年人才能抬动。
开石棺要么暴力破拆,要么就是用巧劲,从一侧沿着缝隙往进凿楔子,让棺盖倾斜,最后依靠棺盖本身的重量,使它自己滑下去。
而在此之前,还要检查一下内部有没有卡槽。
如果有,那四个面都要上楔子,先把卡槽顶起来,然后再提升一侧的高度使其滑落。
这个环节我再度急中生智,提出应该把一侧垫的高一些,这样或许能节省出一点时间。
周伶听完直夸我,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,就谦虚说自己这都是小聪明。
不料她却说:你这不是小聪明,你是大聪明!
唉......
如果不是没时间,我肯定要给她普及一下东北话。
石棺远比想象中要沉。
右边砸下来后,那一侧的墓砖几乎全都被拍断!
好在周伶早有预料,垫砖时她就指挥我们横竖交叠堆放砖块,并将砖跺摆成梯台形状,增强了抗压能力,所以墓砖虽然断了很多,但砖跺并没有要塌的征兆。
接下来,一切都很顺利。
半个小时后,伴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,被铁索捆了四百多年的棺盖,轰然划落!
棺盖落地激起大量烟尘,我们全都退到了中室躲避。
长海叔掏出手台按住:“喂喂,长军,听没听见动静?大不大?”
手台红灯一亮,长军叔说:“还行,我这听着跟山里放了个二踢脚差不多!”
大概过了五分钟,烟尘散消散大半,长海叔立刻招呼大家进去,四把头灯急匆匆穿过甬道,逐一聚拢到石棺旁边。
看清棺内情况,建新哥惊呼道:“卧槽?这老太监没烂啊?!”
没人指责他大呼小叫。
因为大家的注意力,全被棺内景象吸引住了。
是的,没烂。
但很干,皮肤和肌肉组织,全都紧紧贴在了骨头上,黑不溜秋的,看着有点像五香牛肉干。
最为奇特的是,虽然皮肤干瘪,眼窝深陷,但老太监看起来,不但不觉的狰狞,反而还透出一股慈祥之意,尤其他干瘪的嘴唇微微抿起,似带了一抹浅笑,看起来就更显得温和不少。
这让我不自觉的,就想到了爷爷,我感觉老太监下葬时,遗容肯定比我爷爷好看。
这没办法,因为爷爷去世在寒冬腊月,下葬前早冻得梆硬,脸都变形了。
再加上他生前遭罪,不好看也是正常的。
所以我要努力赚钱,给奶奶颐养天年,等她百年之后,让她老人家漂漂亮亮的下去见爷爷!
我知道老太监这种情况,应该叫做干尸,就问周伶是不是。
周伶颔首说:“封闭完好,温度恒定,的确具备成就干尸的条件,不过......”
话一顿,她皱了皱眉,“颜色不太对,估计不是寿终正寝。”
我一惊,顿时想起电视里看过的某些桥段,正想细问时,建新哥大声道:“嗐,管他是正寝还是歪寝,你就是找个姑娘给她侍寝,他也不能自己把东西给咱!伶姐,我翻了啊?”
周伶略微点头:“说的对,找东西要紧,不过下手尽量轻点!”
“好嘞!”
建新哥招呼一声,直接上去翻找,同时嘴里还念叨着:“东家勿怪,借点小财,回头我指定烧几亿新世纪的冥币给你,保证你没见过!”
“卧槽!建新哥你干啥?”
建新接下来的动作把我吓了一跳,因为他一把掀开了锦被,直接朝老太监裆部掏去!
“嘿嘿,这不是太监么?我第一次搞太监墓,研究一下构造,开开眼界!”
“这......”
我本以为,他这种大不敬的行为,必然会遭到长海叔或周伶的呵斥,岂料我看向他俩时,却见他俩也都停下手上的动作,直勾勾等着开眼!
尤其周伶,还用力伸长脖子,完全一副很期待的样子!
来到洼地,长海叔掏出手台按住:“伶姐,我们到了。”
其实他比周伶要大五六岁,但周伶是这次行动的支锅,长海叔就也随着我俩称呼她伶姐了。
伴着少许杂音,手台中响起周伶的声音:“嗯,开始吧!”
打盗洞是个技术活儿。
不同土质打法不同,用的铲子也不一样。
青州这边多是棕壤和褐土,所以当时长海叔他们选择了尖头铲。
速度很快。
建新哥我俩一人提土一人倒土,也要用三个橡皮桶才跟得上进度。
一个半小时后,长海叔他俩接连从盗洞里爬了出来。
“川子,把醋拿来!”
由于知道老太监墓用了浇浆,所以早在出发前,我们就把醋烧热灌进了暖壶里。
但软化合土时,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,盗洞底部空间狭小,人不能留在下面。
辨别有没有毒很简单,闻就可以了。
当热醋浇在合土上后,如果基本只是醋酸味,就说明没毒,如果有明显的臭鸡蛋味,那就是有毒。
这是因为合土中有石灰,古代提纯技术一般,石灰中有可能会含硫。
当醋碰到含硫物质时,就会产生硫化氢,达到一定浓度,是能要人命的。
当然我们并不懂这些,都是周伶告诉我们的。
毕竟我化学只有初三水平,能听明白就不赖了,至于长海叔他们仨,清一色的小学学历......
所以呀,还得好好学习。
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!
很快,一股股热气从盗洞中飘上来,我凑过去闻了闻,还行,不怎么臭。
十几分钟后,长海叔装好探针,伸下去试了试,便按住手台说:“伶姐,合土化开了,下边是墓砖,我让长军过去替你了。”
这也是之前商量好的。
周伶是打金尖,正常来说,要等见了东家才下去,但长海叔说老太监墓不走寻常路,万一在墓里碰到什么突发 情况,我们解决不了,到时还是要叫她下来。
再者说,我们毕竟是拼车,即便周伶信任,也要主动扫清藏私的嫌疑。
手台上红灯一亮,周伶说:“好的。”
趁二人换岗的功夫,我们开始破砖。
墓砖不比石条,只几下,盗洞中就传来噼里啪啦的落砖声。
然后长海叔从包里取出一个罐头瓶,瓶里是半根蜡烛,他将蜡烛点燃,用细线放到墓底,测试下面空间的含氧量情况。
我关掉头灯仔细看着,只见瓶子着地还不到一秒,蜡烛就灭了。
这就说明下边氧气不足,需要通风。
随后我们每隔五分钟试一次,到第三次时,蜡烛就不再熄灭了。
碰巧这时周伶也过来了,建新哥早等的迫不及待,自告奋勇说他第一个下去。
不料周伶却拦住他,回头问我和长海叔谁在上边,得知是我后,她朝建新一指:“你留上边,换平川下去!”
“为…为啥啊?”建新哥不乐意了。
周伶目光灼灼,看着我说了五个字。
“新人手气壮!”
建新哥一愣,随后便麻溜的退到一旁,挤眉弄眼道:“嘿嘿,伶姐这话我同意!”
“川子是新人,这是个新锅,新人干新锅,绝对出大货!”
“赶紧下吧川子,一会再换我下去!”
“给你刷锅!”
我没说话,而是望向长海叔,看他啥意思,结果他直接投过来一个鼓励的眼神。
就这样,我的倒斗生涯,就迎来了第一次下墓经历。
第一次没经验。
六米盗洞,我用了好几分钟才下到底,其间还借助了洞壁上挖好的豁口,却还把手勒的生疼。
反观长海叔他俩,一分钟都没到......
盗洞底部就是浇浆灌顶,合土化开后,被长海叔砸出了一个大洞,经过洞口时我有注意,浇浆层很厚,大概有十公分。
周伶说在古代,这种建筑材料是很费钱的。
待进到洞里,我发现这部分是用砖砌出来的一个半球形,空间很大,几乎和一间卧室差不多。
紧接着,头灯一转,灯光照亮了墓门。
当时,我被深深的震撼了!
石雕仿木的垂檐、门楣、横枋、门簪,门楣上刻有少许祥云浮雕,门扉上装着铜制叩环。
整座墓门将近三米,从上到下皆是原色,没有任何彩绘,给人感觉简洁却不失庄重,似在向我们彰显,数百年前,墓主人高雅的品性。
只这一望,即便我是个盗墓贼,但心里头却也不由自主的升起了一阵肃穆。
长海叔下来后,又将罐头瓶放在靠近门槛的地方。
观察了一会,发现蜡烛的火苗不算高,但暂时看不到熄灭的迹象,说明这里含氧量暂时没问题。
周伶扶着头灯朝门缝照去,随后便拍了下我的肩膀说:“上!”
我当时还在看火苗,冷不丁被她一拍,有点发懵。
“啊?上…上哪?”
“废话!”她白了我一眼,“当然是推门了!”
我呆愣愣看向墓门,心虚的说这玩意纯石头打造的,我一个人能推动么?
长军叔笑道:“没你想那么重,你推下试试就知道了。”
“哦......那行,那我试试…”
深吸口气,我举起双手贴在墓门上。
本以为会很凉,但真正触碰到才发现,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冰寒彻骨,我想这大概是因为,地宫常年保持恒温状态的缘故。
随后我开始用力。
感觉很清晰,墓门动了。
不过只动了一丝,再用力,却无论如何都没反应了。
这情况长海叔他俩都看的很清楚,根本不需要我再解释。
很明显,门后有东西顶着。
周伶示意我后退,再次扶着头灯望向门缝,嘴里嘀咕道:“不应该啊?明明没有自来石,怎么会推不开?”
说着,她双手扣紧门缝,用力将右边那扇墓门给扣了回来,自己又推了一下。
我看的很仔细,墓门只能被推动大概几毫米。
体会着手上的感觉,周伶沉吟道:“难不成......是石球?”
趁着她琢磨的时候,长海叔也上去试了下,完后直接说:“要不上大锤吧!这门看着不厚,上大锤几分钟应该就能干碎!”
周伶摇头道:“最好不要,这里离村子没多远,而且这地方拢音,三更半夜,动静太大了。”
“那咋办?这玩意,在外边指定闹不开啊?”
“哼,那可未必!”
周伶淡然一笑:“叫你侄子把我那个红色 网球包拿下来!”
这群人年龄都在二十五六,全抄着家伙,一看就是专业“办事儿”的!
我一惊,瞬间想到了什么,忙看向周伶。
果然,她脸上不见丝毫的意外。
见我们出来,为首一人开口问:“姓周?”
周伶点头笑道:“大早起的,辛苦各位了。”
“拿钱办事儿,应该的。”那人摆了摆手,并说如果没事了,他们就先撤了。
刚刚那两万块钱一直拎在周伶手里,她直接递给对方说:“还要劳烦您留辆车给我们,另外,经十路上有辆江西牌照的猎豹,麻烦您给弄到市区,多出来的,算我请各位喝茶。”
对方点点头接过钱,挥了下手,人群便乌泱泱开始往出撤。
当时年轻,不懂江湖上的人情世故,所以我就单纯地以为,这群人就是冯爷交钱的原因。
后来我才明白,其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
作为混了几十年的老派把头,哪是区区几十号人就能轻易吓倒的?
他愿意让步,最主要的,还是在于周伶给他通了气儿,而且还安排这群人,等到他从德州赶回来。
否则就算不会闹出什么人命,只要这群人冲进院子,小平头他们就免不了挨顿收拾。
这么做算是给足了冯爷面子。
所以别看他掏了钱,但实际上,却仍是欠了周伶一个不小的人情。
因为对这种老派把头来说,名声和面子,往往比钱重要。
那群人留了辆长安面包给我们。
很破,看着跟出土文物似的,周伶好半天才打着火,不过这已经是他们最好的车了。
开了大概五分钟,建新哥闷闷道:“伶姐,我错了,我不该偷拿......”
周伶面色如常,把着方向盘没说话。
气氛逐渐压抑。
我寻思着应该说点什么,帮建新哥解解围。
不料周伶却突然问我:“平川,你有没有发现什么?”
我一愣,不太确定的说:“伶姐,你问冯爷?”
“对。”
我心道真是想啥来啥,便赶忙说出自己的想法,结果周伶却问我哪不对劲。
这把我给难住了。
毕竟我只是恍惚的有那么一种感觉,具体哪不对,一时间却说不上来。
于是我仔细琢磨起来,一遍遍回忆着冯爷看银锭的一幕。
忽然,我意识到什么地方不对了!
“伶姐,我感觉最先引起冯爷注意的,不是银锭,是宝贝罐儿!”
“而且我觉的,他看见罐子那会,其实是非常惊讶的,但他却克制住没表现出来,然后他问银锭应该也是故意的,这就有点怪,我觉着他好像......好像有点不想让咱看出来他在惊讶。”
本来之前没想到这么多,但经过这么一分析,我越发坚定自己的判断了。
冯爷在刻意的掩饰着什么。
虽然他表现的很完美,但打从他进屋后,我的注意力一直在他身上,所以就被我发现了。
换句话说,如果他看见罐子时直接提一嘴,我肯定就不会觉得奇怪了。
毕竟那玩意挺少见的。
周伶唇角一勾,似笑非笑道:“看来这罐子,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啊......”
我心说难不成她打眼了,罐子很值钱?
但细一琢磨,又觉得不太可能,于是我便问她接下来干嘛。
“不急…”周伶慢悠悠道:“冯抄手毕竟老 江湖了,他有这么一号,就是因为做事谨慎,喜欢留暗中出手,即便这里边有什么猫腻,他也不会立刻行动。”
“所以咱该干嘛干嘛!”
“见买家,出货!”
......
齐水之滨,古韵泉城。
这座城市里,曾留下我很多回忆,而回忆开始的地方,在南郊宾馆。
午后一点,房间里陆陆续续来了四个人。
这里出了点小差错。
原本周伶只约了三个买家,一个济南本地人,叫郝建民,两个江西来的,王兴和乔志斌。
但乔志斌又带来一个叫黄波的本地古董商。
这人色眯眯的。
打从一进屋起,他那双贼眼就时不时的往周伶身上瞄,虽然我没事儿也看,但我完全是欣赏,跟他不一样。
对此乔志斌解释说,上午捡漏儿来着,担心刀子钝,就临时拉了外援,并一再保证不会出问题。
之前周伶说过,我们这次货杂,需要庄子对口才卖的上价钱。
原定三人里,郝建民是玩儿玉器和青铜器的,王兴主打瓷器明器,而乔志斌则是专收“红薯”的。
红薯就是窖藏货,即金银锭和铜钱。
也就是说,我们这次的大头儿,主要靠他跟姓黄的。
再加上周伶和乔志斌合作过好多次,也就没说什么,直接示意我往外拿东西。
我第一件掏的是那件乳白色珐华香炉。
剥开泡沫纸的瞬间,王兴就猛地站了起来。
“嘶~”
“好东西!!”
他上手摸了摸,兴奋的问:“全不全?”
“这是自然。”
周伶拿出相机给他看照片,王兴瞅了几眼,直接伸出两根手指。
周伶点点头没说话。
倒是黄波皮笑肉不笑的说了句:“呵,王老板真是豪气!”
珐华香炉属于五供中的一件,昨天拍照时周伶跟我讲过,这五样东西如果单卖,一件平均三到五万左右,合起来则能翻上一翻。
当然了,这是市场价。
我们作为一手货源,单件也就一到两万,合起来卖到十万就不亏了。
王兴直接给二十,不是因为他人傻钱多,而是他有经验。
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,他一见这东西,就猜到我们后边还有好货,所以先打了个样儿,这么一来,其他两伙人也就不好意思太抠搜,等再有适合王兴的,周伶则要让些价格还人情。
第二件只有照片,是玉如意。
郝建民不像王兴那么痛快,跟周伶磨了半天才给到一万七。
接下来就是他俩交替看货。
最后全套五供、青花梅瓶、渐变色琉璃盖碗以及其它器皿,王兴六十方一枪打了。
这个价格对我们来说不低,对他而言也有不小的赚头。
别的不说,只那一件梅瓶,他就能回本一半。
而且这还是当时的行情。
如果放到五年后,就算不是元青花,这件东西也能让他大赚一笔。
至于所有小件玉器首饰、文房四宝以及那枚云鹤纹铜镜在内,郝建民也是一枪打,共计十五万。
其中歙砚占了大头,一件就是六万。
这已经接近当时的市场价,郝建民肯出这么高,说明他手上肯定有专门收藏古砚的下家。
而我最喜欢的那枚红鱼带钩,居然才卖了六千块钱!
我心说等分了钱我就去找他,只要他别太过分,我就买回来!
见二人结束,乔志斌站起来搓了搓手:“诶哟喂,佢俚两个总算搞完哩哟,咯下子该轮到我哩哟!”
“小伶诶,快些子把东西拿出来啵,也好让大家都开下子眼界噻!”
见到那东西的第一眼,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。
是一枚带钩。
带钩主体呈鲤鱼样式,腹依水浪,背托莲花,鱼身修长优美,线条自然流畅。
再加上是西红的料子,灯光一照,手掌便被映的通红,仿佛下一秒,它就要跃出掌心,畅游而去......
我几乎看入迷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,何为器物之美。
越看越喜欢,完全爱不释手。
很快......
一个难以抑制的想法,就从我脑子里升腾起来:这是我发现的,我想要这件东西,我可以把它偷偷装进兜里,不告诉大家。
不是因为它的价值。
真的,我那时也不知道它的价值,我甚至连它叫什么、干什么用的都不清楚。
我就是纯粹的喜欢!
当时我攥着带钩,手都到裤兜边上了。
但最后,还是没放进去。
长海叔照顾我,愿意让我跟着他出来挣钱,建新哥待我更像亲兄弟一样,还有长军叔和刚刚认识的周伶,对我也都不差,我不能昧着良心,做对不起他们的事儿。
而且就算不提他们,我要是这么干了,自己也会瞧不起自己的。
呼——
轻吐口气,我摊开手再次看向带钩。
妈的,沾了汗之后,它特么更漂亮了!
但这次我没再纠结,扯出泡沫纸便将其包好,装到了编织袋里面。
接下来,我又翻到了一枚青玉帽正、三颗栗子大小的蜻蜓眼、一支银质发簪,一枚小指粗细的玛瑙勒子,还有三十几枚弘治隶书小平钱。
看着面前大大小小的泡沫纸包,我相当满意。
我心想周伶说的真是没错,新人手气确实壮,碎布片里也能摸出宝贝来!
后来我才知道,根本就不是我运气好,而是但凡这种老辈子的木箱,里头都会有点值钱的小物件。
因为古人有个习惯,叫做“压箱底儿”的。
这种习惯并不局限于陪葬品,活人用的箱箧匣柜一样如此。
有的会直接放在里面,有的甚至会做成夹层,专门用来存放首饰银钱。
所以直到今天,依然还有不少人专程跑去乡下,走街串巷的收这些老箱子,别以为这群人是吃饱了没事儿干,都是冲着你祖宗的压箱底儿去的!
此外当时周伶告诉我,这两个木箱,也是这座墓里比较异常的地方之一。
按理说,老太监墓用了整体浇浆,封闭性极好,衣服被褥之类,应该能保存的鲜亮如新才对。
再有就是成箱的衣物,一般都会放在主墓室里靠近棺椁的位置,这样才更贴合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的理念,仿佛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,也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这些衣物。
但在老太监墓中,却并没有这么安排,至于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,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当然,这并不影响我们。
只要他不放进阴间,放哪都不影响我去搬!
不对,也影响。
烂了就没法搬了......
和我比起来,长海叔那边是一毛没有。
西侧壁龛里都是书画,和衣服一样,一碰就碎成渣渣。
周伶倒是翻出点东西。
东侧壁龛里放的是文房四宝,她从里头拿出了一方歙砚、一口绿釉笔洗、一块寿山石镇纸,此外还有两根笔杆,是犀角的,不过毛掉光了。
歙砚主题为“老子西出”,雕工十分精湛,周伶说这题材她第一次见,是高货。
完后她跑到西侧壁龛仔细翻了翻,发现确实啥也不剩,便有些失望的说:“这老太监书画造诣应该不赖,可惜墨宝没留下来。”
我转了转眼珠,上去安慰说:“伶姐,这人连名都没留,就是有,也不一定能值钱的。”
“呵呵,要真有一张他的字画保存下来,我让它能比这里所有东西加起来还值钱!”
听见这话,我话都说不利索了,结结巴巴的问为啥。
不料周伶却摇摇头道:“一句两句说不清楚,先干活吧,长海大哥,你先把这几袋东西送上去,平川跟我去后室。”
一说要进后室,我心里便泛起一阵激动。
后室就是这座墓的主墓室,会放有墓主人的棺椁,最值钱的陪葬品,往往也会放在棺椁中。
换句话说,我们就要和老太监见面了!
虽然不清楚他身边,具体会放些什么类型的宝贝,但我通过周伶的反应能看出来,只凭目前找的这些,她就已经回本儿了,而且还有得赚。
之前她曾许诺保我们二十的车费,照这么一看,目前的收获,保守估计,恐怕也得在三十朝上!
前菜都这么丰盛,重头戏肯定也不会差!
想到这,我快步跟上周伶,钻进了后甬道。
可不知怎的,她却没往前走。
她冷不丁一停,导致我整个人都贴了上去。
由于怕被当成流氓,我触电似的往后一趔趄,连忙说:“哎~对不起啊伶姐!不过你干嘛突然停......!!”
话音戛然而止。
我知道她为什么停下了。
漆黑的墓室中,一具青灰色的石棺,被八条铁索层层缠绕,悬吊在棺床上方!
居然......是悬棺?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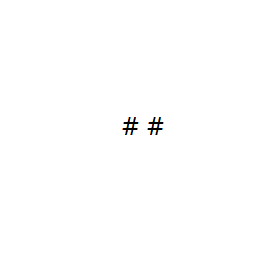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